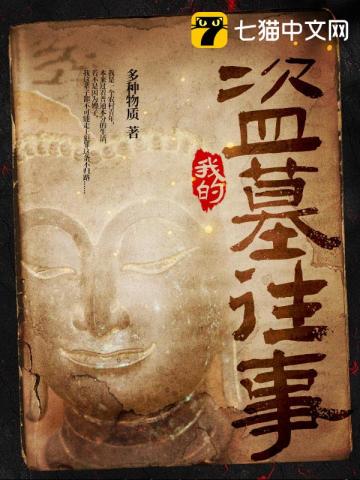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但愿爱情明媚如初(出书版) > 第50章(第2页)
第50章(第2页)
我恨不得会分身术,可是我不会,于是只好风驰电掣地驶回旅馆。我妈果然在旅馆外等我了,手脚冻得连弯儿都不会打了。我抱住她,玩儿命地搓:“给我打电话啊,担心我就给我打电话啊。”
我妈没说话,挣开我,一瘸一拐地先进了去。
天不亮,我又折回了周森家。还正是车少人稀的时候,我拐最后一个弯的时候也没减速,险些撞上人,一颗心吓得脱了缰似的,然后再一定睛,那人正是周森。
周森没开车,步行着,才回家的样子。我的车灯打在他身上,晃得他下意识地眯了眼。
我突然像被灌了大口大口的海水,眼泪止不住地掉。我火冒三丈,啪啪地将大灯开了关,关了开,大有不晃死他不罢休的架势。
周森自然绕过来,要开我的车门。我手疾眼快,上锁,接着就要踩油门。
周森两步又折回车前,以卵击石地将手按在我的车前盖上。
可我到底也不能从他身上碾过去。
我气急败坏,下了车,摔上车门:“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有没有资格问你去了哪?”
周森又使出他滴水不漏的杀手锏,利落地脱下大衣,划着完美的弧度披到我的背上。这一系列动作给他争取了时间,最后他权其利弊后,说:“有。”
可我再没说一句话,光狠叨叨地瞪着他。要是我当时有面镜子,我会知道我自认为的狠叨叨,根本是没出息的哀怨。
周森一直在等着,等着我发问。
而我将大衣甩给他,扭脸便回到车上:“我说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问完了,你也回答完了。”
我这辈子没这么孬种过,人家让我问了,我却不敢问,人家摆明了要坦白从宽,我却不敢审判。我又一次锁上了车门,这回是铁了心要一走了之。
周森大概这辈子也没这么狼狈过,他拍打着我这一侧的车窗,追着我的车对我喊着:“突然有急事,我不得不去处理。你给我打电话了是吗?我的手机没电了。心沁,我的手机没电了……”
我狠踩下油门,几乎带倒了周森。
再过四个半小时,我的手机又该滴滴作响了,那个倒计时的定时,将要提醒我我和周森只剩三天了。我设定这个定时的初衷渐渐失了效,我根本是在二十四小时地一触即发,每一分每一秒都像灾难。我早就不是那个坚强,或者故作坚强的我了,而周森也不是那个泰然,或者故作泰然的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