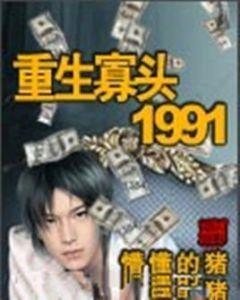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我真没想火葬场啊[快穿] > 第45章(第2页)
第45章(第2页)
质疑他本人没问题——宁阳初自己都赞同那些人说的话,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根本没什么本事,不过就是个运气好的花架子。
但质疑团队就其心可诛,宁阳初大半夜气得满头汗,死死咬着牙,跟阴谋论者对着吵:你才洗地,你才包庇,你才被人卖了还帮忙数钱。
他一天都不能等,现在就要回去训练,再把过去的数据和团队会议记录砸在这些人脸上。
所以他火烧火燎拆酒吧,把能卖的酒柜和桌椅全都卖掉。
这里要盖旅游区,以前是暴发户的项目,这几天暴发户资金流蒸发破产,到处躲债,这一片就转手给了新的投资商。
新投资商有别的产业,酒保们不过换个地方工作,半点不影响拿工资,明天就能去新酒吧上班。
酒保们都挺乐意,因为新酒吧条件更好,工作轻松、奖金丰厚,还不用面对莫名其妙的神经病客人。
宁阳初找人拉走了一车桌椅,他把门关上,回到空荡荡的酒吧。
神经病还坐在角落不动。
好像这样就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好像这样就能让回不来的人回心转意。
痴人说梦。
“……有酒吗?”裴陌的声音很沙哑,“随便什么酒。”
宁阳初去拿外套:“没有。”
酒窖里的酒都被送去了该去的地方,给配喝他们的人喝。
这个酒吧里的两个人,都不配去那个地方,不配喝酒,不配认识温絮白的朋友。
他的态度格外冰冷,裴陌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只是继续说:“……你现在需要钱。”
宁阳初的脚步停顿。
“你要钱,复健训练,给……温絮白正名。”裴陌盯着空气里的某处,嗓子嘶哑空洞,有些字眼甚至听不见声。
他现在能说出这个名字了,但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简直像是已经被什么孤魂野鬼掏空了,只剩个腐朽稻草勉强搭起的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