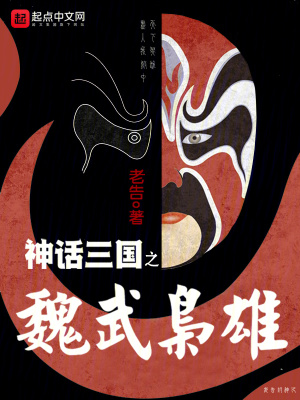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妾妻 > 第89章(第1页)
第89章(第1页)
“三夫人,小心!”玢儿失声喊起来,又将尾音咬进了肚子里。
圆仪侧头剜了她一眼,继续朝前走。王剑就候在假山后头,暗夜里一个颀长黑影举着一柄油纸伞,幽幽立于如丝春雨中。圆仪和玢儿走近了,玢儿福了福,将伞与灯笼递与圆仪便识相地跑开。王剑举着伞走到圆仪跟前,长身玉立,神情潇洒,圆仪待要说话,他却一把拿过圆仪手里的灯笼,“噗”一口气吹灭了。圆仪不解,王剑却已俯身搂住了她,圆仪一惊,手里的伞落到了地面上,连着里子一起被雨打湿。
“再让我抱你一次,就一次!”王剑恳求。
静寂的黑夜中,王剑一手举伞,一手搂着圆仪,圆仪静静地伏在他的胸前,心却平静如湖,泛不起任何涟漪。甚至她的脑海里不停地翻闪出赵士程的影像,心底里负疚的感觉就越发弥深。圆仪使劲推开了王剑,退到了雨中,春雨如酒,油油地飘洒在她的面庞上,没有令她醉,却令她越发清醒。王剑上前一步,用伞遮住了她的身子,失落却依旧担忧道:“你小产不久,不要淋雨,免得落下病症。”
圆仪苦笑:“病根横竖是落下的了,你说过我滑胎两次,恐难再有孕了,我终是福薄之人,不比悠悠……”
“你之所以可能无法再怀孩子,悠悠有莫大的责任,要不是她,我们的孩子……”暗夜里,圆仪看不见王剑的脸,只看见一团黑魆魆的怨气,一股冷风夹着雨丝刮过脸颊,她倒抽一口冷气,打断他的话,道:“事已至此,别再说了!”
“夺妻之恨,丧子之仇,怎能善罢甘休?”
“你已经持续给她下药,她的身子多半也被你弄坏了,你还要怎样?”不知为何,圆仪心底是不忍心的,每个夜晚她都在睡梦中反复问着自己是不是对悠悠的怪责太过牵强?
“光弄坏她的身子,怎能泄我心头之恨?我还恨不能要她和赵士程的孩子给我们的孩子陪葬!”
“你不能这么做!”圆仪厉声说道。王剑怔了怔,黑蒙蒙的雨夜里他分明感觉到圆仪目光中的不忍,只听圆仪颤声道:“婉姐姐不能生育,我能不能生育是个未知数,公子就修儒一个孩子,你不能让公子断后。”
王剑猛地向后踉跄了一步,许久他苦笑道:“原来再弥深的山盟海誓亦抵不过耳鬓厮磨的朝朝暮暮……”王剑说着,心灰意冷,弃了手中的雨伞,越过圆仪蹒跚地在春雨中走远。
圆仪在雨中站了许久,春雨斜飞细飘的,濡湿了她的头脸,直至一盏灯笼从远处飘来,玢儿拾起地上的雨伞慌乱地遮住她头顶,道:“三夫人……”灯笼橘红的灯光中,玢儿看见圆仪满脸潮湿,不知是雨是泪。
“夜深了,回房去吧!”玢儿小声恳求。
圆仪不再拒绝,任由玢儿搀扶着,软软走回如意轩去。
赵府开始张罗修儒的满月酒和赵士程的纳妾事宜,因为吱吱是府内丫鬟收房,自是不比悠悠从杭州嫁过来时的排场,一切从简,只将赵府内紧挨着绿绮轩的兰桂轩收拾出来做为新房,也不必小轿从侧门过,省了一应拜天地的仪式,只等着修儒满月那天,吱吱向唐婉、悠悠、圆仪敬过茶之后,当夜与赵士程圆房即可。离修儒满月还有数日,吱吱是一边心怀忐忑等着做新嫁娘,一边又不敢放松对悠悠和修儒的照顾,生怕一个不小心就遭了王剑的毒手。王剑见悠悠日渐憔悴萎靡,只当是自己的**渐渐显效,便也不仔细请脉,想着极早抽身,便跟赵士程请辞回杭州。赵士程强烈挽留他喝过满月酒后再走,又有圆仪央求他留下
,他便继续呆在赵府。他知道他必须再替圆仪做一件事方能功成身退。
修儒满月的日子转眼便至,淅淅沥沥的春雨终于停住,天气放晴,神清气爽,满月酒席摆满赵府所有宴会厅,山阴城内达官贵人悉数到场,怎一个盛大奢华了得。午后,满月酒席结束,赵士程与唐婉、悠悠候在前厅,等着吱吱来敬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