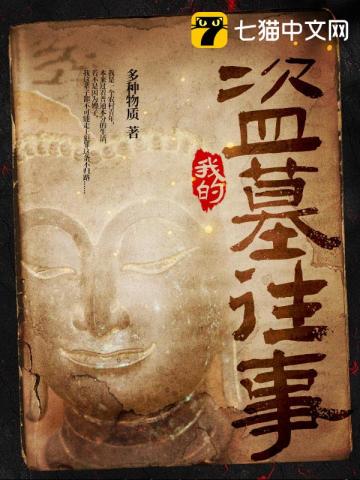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如是说(先婚) > 42(第3页)
42(第3页)
鄢琦闭了闭眼,随口说了一句,“洛杉矶,davidson老师最近在那边。”
他松开钳制,转而抚平她衣领的褶皱,动作温柔得像在对待易碎品,可另一只手背却暴起青筋。
就在关铭健俯身想再说什么时,房门突然被敲响。
“姐夫?”敲门声突兀地响起。鄢以衡刻意提高的声线穿透门板,“爹地让我来看看——hf银行的陈行长到了。”
关铭健的指尖在她颈动脉流连,她的脉搏在他指下急促跳动。他俯身时,忍住负面情绪,依旧保持着温和:“我们晚上慢慢商量,嗯?”
“我让厨房重做你爱吃的松露炖蛋,待会送上来。”他整理着袖扣,目光却目光分毫不离她的脸庞,“我很快回来。”
鄢琦低下头,失去和他对视的勇气,而他转身开门时,又恢复了那副无懈可击的模样。
房门关上的瞬间,梳妆台上的香水瓶砸落在大理石地板上,柑橘调的香气在空气中炸开,分明该是夏天的明媚,此刻全是果皮的酸涩。
有人爱她,却不想读懂她的灵魂。
这比漠视更残忍,鄢琦跌坐在床边的波斯地毯上,眼眶灼热发疼,却流不出一滴泪。
——我不是他的蝴蝶标本。
向来尖锐的ivy此刻声音里竟带着迷茫,像被困在玻璃罐里的萤火虫,明明灭灭。
“小姐。”门外传来叁声规律快速的轻叩,管家珍姐在门外恭恭敬敬地叫了她几声,“sir请你落去书房。”
“……好。”她扶起摇摇欲坠的身体,指节无意识地揪紧裙摆,一步步走向二楼会客厅旁的书房。
二楼走廊的壁灯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经过会客厅时,那架施坦威钢琴上还摆着今早插好的白玫瑰,花瓣边缘已经泛起褐痕。
佣人看见她靠近,主动打开书房大门,鄢鼎背对着门站在落地窗前,雪茄烟雾模糊了他的轮廓。听见门响,他转动拇指上的翡翠扳指:“坐。”
“爹地。”她站在波斯地毯边缘没动,嘴唇苍白干燥,眼神却不自觉落到茶几上的水晶烟灰缸。
鄢鼎弹了弹烟灰,转过身来,审视着女儿的神态,“alex最近同mr.comwsan走得好密。你知唔知佢哋倾紧咩?(他和洛桑先生走得很近,你知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鄢琦盯着父亲定制的意大利西装肩头的褶皱:“我唔过问佢公事。(我不过问他的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