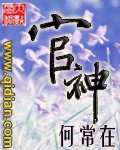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大明:朱重八的六岁小皇叔 > 第212章 和尚,你的茶凉了(第3页)
第212章 和尚,你的茶凉了(第3页)
他将碎片拼起,镜面里不再是单一的场景:左边是长安的书院,学子们正用扶桑的宣纸抄经;右边是大阪的工坊,织工们将《诗经》的句子织进锦缎。
中间是釜山港的码头,两国的工匠正合力铸造新的“同量”碑,碑石上既刻着汉文的“公平”,也刻着假名的“共生”。
“师父,”小沙弥指着经卷的夹缝,那里有几缕新的光纹正在生长,“这些光是从哪里来的?”
智海望向窗外,市集上空的光纹正越聚越密,像一条七彩的河。
他想起弘景法师的话,轻声道:“是从人心底来的。”
半年后,阿雪的“日月同辉”屏风终于织成。
屏风展开时,长安的朱雀街与奈良的春日大社在锦缎上遥遥相对,中间是片波光粼粼的海面,无数细小的光纹在浪涛里闪烁。
那是两国百姓交换的信物:蜀锦的线头,扶桑的贝壳,长安的铜钱,大阪的稻穗。
国王亲自为屏风题字,写的是“和而不同”。
墨迹未干,智海带来的《礼记》突然金光大盛,将四个字映得透亮。
屏风上的光纹应声而起,化作真的光影投在墙上:有大周商人教扶桑农户用曲辕犁,有扶桑工匠帮唐人修补漆器,还有个穿唐装的扶桑姑娘,正把樱花枝插进长安的青瓷瓶。
那天夜里,大阪港的茶摊亮到很晚。
大周商人与扶桑米商借着月光对账,算珠碰撞的声音里,“公平”的光纹渐渐与月光相融。
智海看着他们,手里的唐镜突然清晰起来——镜中不再有任何画面,只有一片温暖的白光,像极了他初见长安时,青龙寺后院的阳光。
远处,“拓海号”商船正扬帆起航,新帆上的“同舟”纹样在月色下泛着柔光。
甲板上,阿雪的弟弟正用刚学的汉字写家书,笔尖的“友”字光纹落纸上,立刻与信纸里的“亲”字光纹缠在了一起。
智海轻叩念珠,檐角的铜铃又响了。
这一次,铃声里没有争执,只有风穿过光纹的清响,像无数根丝线在天地间轻轻颤动,织着一幅永不褪色的锦缎。
喜欢大明:朱重八的六岁小皇叔请大家收藏:()大明:朱重八的六岁小皇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