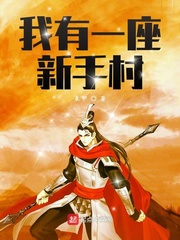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大明:朱重八的六岁小皇叔 > 第215章 互相融合(第2页)
第215章 互相融合(第2页)
他把算珠归位时,指尖的“度”字光纹重新凝聚,比从前更亮了些。
老兵在货箱垒的墙后睡着了,怀里还攥着那片刻“风”字的船桅碎片。
阿雪给他盖锦缎时,发现碎片背面竟刻着行小字:“开元十七年,与太郎同修此船”。
她突然想起昨夜那个叩首的小卒,他怀里护身符的“福”字边角,也有个模糊的“太郎”印记。
原来有些名字,早被海风刻进了彼此的骨血里。
三日后,“拓海号”要往广州湾送消息,老舵手却在货舱里多装了些东西:阿雪新织的“樱花缠枝锦”,智海抄的《礼记》残篇,板垣算好的“唐与扶桑度量衡对照表”,还有老兵磨亮的船桅碎片。
“告诉那边的人,”老舵手拍着船舷,“共津的铜铃还在响,只是换了个调子,像当年商船靠岸时那样,带着糖霜味。”
船开时,阿雪的弟弟往海里撒了把种子,有长安的稻种,也有从黑浪军箭袋里捡的扶桑粟米。
海水漫过种子时,竟泛起细碎的光纹,稻种的“农”字与粟米的光纹缠在一起,沉向海底那片曾波动的光纹网。
“等它们发芽,”少年望着船影,“说不定能长出既结稻穗又结粟米的禾苗。”
智海在码头牌坊的碎石旁立了块新碑,没刻“四海之内”,只刻了个“缝”字。
他刻到一半时,发现石缝里钻出株嫩芽,根须缠着半片锦缎,上面的青花与白棉线正顺着根须往土里钻。
“你看,”他对蹲在旁边的阿雪说,“不用我们动手,它们自己就在往一起凑呢。”
暮色再临时,有艘小渔船摇摇晃晃驶进码头,船头站着个穿粗布衫的扶桑人,手里举着块锦缎,正是阿雪昨夜补的“四海之内”残字。
“我是黑浪军的逃兵,”他声音发颤,“将军说要烧光唐物,可我娘说,我爹当年在长安学的织锦,是用来做嫁衣的,不是裹尸布。”
他从怀里掏出个木盒,里面是枚铜镜,镜背刻着“友”字,边缘却镶着扶桑的螺钿。
阿雪接过铜镜时,镜里映出码头的新景:波斯商人在补香料袋,天竺僧侣在晒佛经,老兵在教少年们用船板拼“和”字,连板垣的算盘都在算“明日该进多少扶桑漆料”。
镜光晃了晃,竟映出黑浪军退去的船队里,有艘船悄悄掉了头,船桅上的“征”字旗被人换成了块粗布,上面用锅底灰写着个歪歪扭扭的“商”字。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