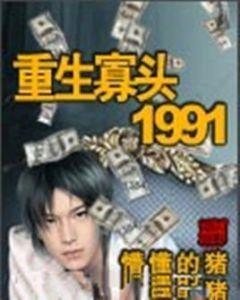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妒烈成性[重生] 作者:刑上香 > 第210章(第1页)
第210章(第1页)
地上死士一只手颤抖着欲抓起匕首,却是被一只锦靴碾过手腕。
骨骼尽碎。
卫瓒却视若无物, 面无表情踏了过去。
随风在身侧低声问:“这些人怎么办?”
卫瓒说:“就地格杀。”
“问不出什么, 留着也是祸患。”
随风应了一声“是”。
枪尖还染着红,面具上也沾了点点血痕。
随风似乎已是习惯了,那位他自小追到大的小侯爷,独自在外时, 总是含着几分冷漠,这短短一年的功夫, 却越发与靖安侯神似,甚至比那位久经沙场的靖安侯还要冷上三分。
将领的冷漠是残忍的, 亦是可靠的。
倚在门边的卫瓒却仿佛听着了什么声音似的, 微微皱起眉,那声音自远处而来, 逐渐由远及近,最终他伸出染血的手, 却是接过了一只雪白的鸽子。
他解下鸽足上细小的竹筒,细看了半晌, 却是拧起眉来,半晌轻声道:“京北大营异动。”
安王这一世没了死士, 便借着昔日质子的名声, 隐有拉拢驻京四营的态势。
卫瓒心里头有数, 便早早在各营扎了眼线。
如今京北大营一动,卫瓒便立时觉着事态不对。
正是思忖之时,便见又飞来一只白鸽,卫瓒只拆了信一瞧。
是沈鸢的字迹,清隽雅致,寥寥数字,大意是已得了状元,准备赴宴。只是昨日会文殿走水,今日御宴照常进行,改安排在宫外的皇家别苑。
另有辛人,欲观礼于侧,圣上已准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