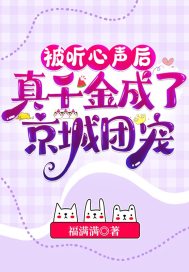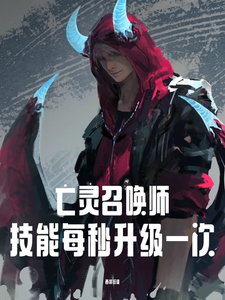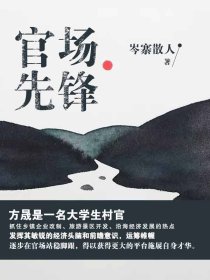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十国风华 > 第二百二十七章 京城风云(第1页)
第二百二十七章 京城风云(第1页)
两人在凉棚下坐定,凌冽的寒风吹拂而来,郭荣的目光变得深邃:“王峻回京短短几日,朝堂上便翻了天。他说卫州赈灾耗费过巨,奏请陛下削减各州粮援,还说……你行事狠辣,受灾百姓吃糠咽菜,与陛下仁德之名有损!”
杨骏当然知道王峻回去不会给他添好话的,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随即释然一笑:“意料之中。王相要的,从来不是卫州安稳,是他自己的权势稳固。”
“陛下没准。父皇说,‘杨骏在黄河边扛石头,总好过在京城耍嘴皮子’。但王峻不会善罢甘休。他削减粮援是假,想逼你出错是真——卫州的粮食,怕是要断了。”
杨骏心中一凛。他早猜到王峻会有后招,却没想来得这么快。他抬眼看向郭荣,见对方眼中并无幸灾乐祸,只有坦诚:“侯爷特意绕道卫州,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噩耗?”
郭荣浅笑一声道:“人们常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这种情况下我若是只是简单给你说这些消息的话,那我就不用单独跑这里一趟了!”
说完这话后,郭荣从袖中取出一卷帛书,推到杨骏面前,“这是澶州军仓的调粮令。五千石糙米,三日后从白马津运过来,用的是军粮的名义,王峻查不到。”
杨骏展开帛书,上面的朱砂印鉴鲜红夺目,是郭荣的私印。他抬头看向郭荣,对方正望着黄河水面,轻声道:“去年我在澶州赈灾,也遇过粮荒。那时才明白,百姓要的从不是谁的权势大,是锅里有米,身上有衣。你在这里搞的‘工分兑粮’,父皇在密报里看过,十分赞赏,说这法子,比十个节度使还管用。”
杨骏心中一热,握着帛书的手指微微发颤。他原以为自己在卫州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困守孤城般的挣扎,却没想千里之外的京城,竟有人真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侯爷就不怕,这卷调粮令落到王峻手里,成了你的把柄?”
郭荣浅笑一声,笑声里带着几分少年人的坦荡:“我若怕,就不会来见你了。王峻想挡我的路,挡不住;想断卫州的粮,也断不得。”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望向堤坝的方向,暮色已浓,那里的火把又亮了起来,蜿蜒如火龙,“杨骏,这天下,终究是百姓的天下。谁能让他们活下去,他们就认谁。”
杨骏也站起身,与他并肩而立。黄河的涛声在夜色里愈发清晰,混着堤坝上隐约传来的号子声,像是大地的心跳。远处的灾民棚屋里,亮起了点点油灯,昏黄却温暖,那是无数个家庭在灾劫里守着的希望。
杨骏随之起身,肩并肩立于那人的身旁。夜色深沉,黄河的轰鸣愈发震耳欲聋,它奔腾不息,与堤坝上隐约可闻的劳动号子交织在一起,宛如大地深处沉稳而有力的脉动。远方,灾民搭建的简陋棚屋星星点点地点亮了昏黄油灯,那微弱而温暖的光芒,在寒夜里闪烁着不屈与坚持,是无数家庭在灾难的阴霾中紧紧守护的微弱却坚定的希望之光。
“我提这里的百姓谢过侯爷,救命之恩如再生父母,这里的百姓将永远铭记。”杨骏的声音柔和而坚定,每一个字都承载着前所未有的真挚与感激。
郭荣轻轻颔首,稍作停顿后,语气中带着几分郑重道:“关于灾情之事,暂且言及于此。另有一事,你需多加留意,切莫忘却。下月童子试在即,你务必要及时赶回。这件事做好了,对你来说,可是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