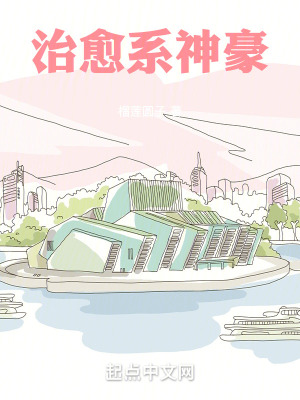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重生朱雄英,复活白起灭倭国 > 第342章 蓄势待发(第1页)
第342章 蓄势待发(第1页)
“说好的昨日就该到了!这都什么时辰了?日头都快偏西了!蓝玉那厮带的什么兵?爬也该爬到了吧?!还有我那大侄子!莫不是被哪个不开眼的边城小吏绊住了脚?”
朱樉越说越气,蒲扇大的巴掌“啪”地一声拍在旁边一个硬木矮几上,震得上面几个粗陶茶杯叮当作响,“老子三万儿郎,刀都磨得雪亮了!马都喂得膘肥体壮!就等着砍鞑子的脑袋当球踢!这倒好,在这儿干耗着,喝西北风!”
他猛地停下脚步,瞪着铜铃般的眼睛扫视帐内其他三人:
“老三,老四,十七!你们说,急不急人?!”
晋王朱棡端坐于主位左侧的一张铺着虎皮的宽大座椅上。
朱樉虽然比他他年长几岁,但朱棡更为面容方正,气质沉稳。
一身绛红色的亲王常服外罩着轻便的锁子甲,显得不怒自威。
此刻,他正慢条斯理地掏出一包华子,抽出一根点上。
经过前段时间随朱雄英的“发泄疗法”和“烟物疗法”,他的狂躁症基本没有复发过了。
朱棡闻言只是呼出一股青烟,眼皮都没抬一下,淡淡道:“二哥,稍安勿躁。军情大事,岂同儿戏?蓝玉治军严谨,雄英更是少年老成,他们迟到,必有缘由。或许是路上遇了状况,或许是处理了些许军务耽搁。急有何用?”
朱棡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天然的威严,如同磐石般沉稳。
坐在朱棡对面下首位置的燕王朱棣,则显得更加内敛。
他一身深蓝色劲装,外罩着半身鱼鳞甲,姿态放松地靠在椅背上,手中把玩着一瓶茅子。
他面容英俊,眼神深邃,嘴角似乎总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听到朱樉的抱怨和朱棡的劝解,他微微一笑,接口道:
“三哥说的是。二哥,你这脾气,几十年如一日。”
“雄英那孩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做事极有章法,比咱们当年可稳重多了。说不定是路上见哪处民生凋敝,停下来体察一番,顺手收拾了几个不开眼的蠹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