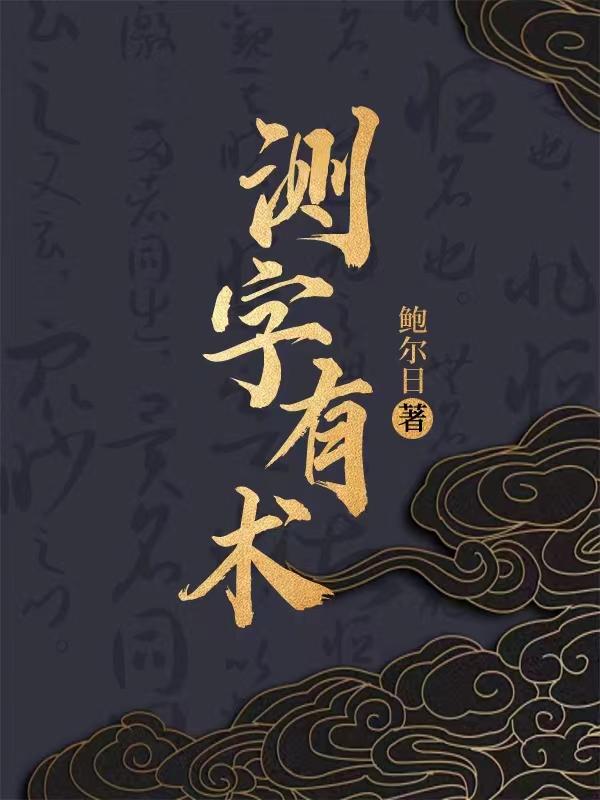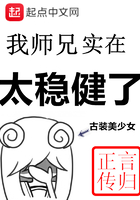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新生1970 > 第183章 言情文中的炮灰12(第1页)
第183章 言情文中的炮灰12(第1页)
细雨飘得正绵,田埂上人影晃动,公社的严书记刚在田头嘱咐完排水的事,特意拉过几个相熟的妇女:“这雨下得久,地里干活的人怕是冻着了,你们辛苦一趟,回村凑些茶壶,去知青点找王知青,他那儿烧了姜汤,多装点送去给大家暖暖身子。”
几个妇女应声应得脆,各自往家赶,有的翻出藏在柜子里的搪瓷茶壶,有的敲开邻居家门借陶壶,很快凑齐了五六只壶,急匆匆往知青点去。路过玉米地时,见王杰拄着棍子往回走,裤腿卷到膝盖,泥点子溅了满腿,其中一个姓张的大嫂赶紧上前:“王知青,严书记说了,让你先回点上歇着,我们来拿姜汤。”说着不由分说搀住他往回走。
刚进知青点灶房,那几个妇女也提着壶跟了进来。王杰掀开锅盖,大锅里的姜汤正咕嘟冒泡,两口小锅里的红糖块已化得差不多,红亮亮的汤汁裹着姜香扑面而来。“哎哟,还放了红糖!”张大嫂眼一亮,咂着嘴直夸,“王知青真是大方,这红糖金贵着呢,平白让你破费了。”
“就是就是,”旁边的李大嫂也跟着说,“俺们家过年都舍不得这么放红糖。”
王杰笑着摆手:“看大嫂们说的,大家在地里冻了两天,喝点热乎的驱驱寒是应该的,都是为了地里的庄稼,谈不上破费。”
说话间,妇女们早把茶壶涮干净,轮流往壶里舀姜汤,搪瓷壶、陶壶很快都灌满了,连带着有人从家里带来的粗瓷碗、铝制茶缸也都盛得满满当当。张大嫂拎起最重的那只壶:“俺先去水稻田那边,那边人多!”其他人也跟着应和,踩着泥路往地里赶,壶里的姜汤晃出热气,混着细雨,在田埂上拉出一道道暖烘烘的线。
妇女们踩着泥路往田里赶,壶里的姜汤晃出阵阵热气。到了玉米地边,张大嫂先扯开嗓子喊:“都歇会儿,来喝口热的!王知青在知青点煮的姜汤,还放了红糖呢!”
正拿铁锨挖渠的村民和知青们闻声围过来,手冻得通红的赶紧接过茶缸,滚烫的姜汤下肚,一股热流从喉咙直窜到肚子里,连带着冻僵的手脚都活络了些。有人咂着嘴叹:“这姜汤够劲,还甜丝丝的,暖和!”
李大嫂一边给大家续汤,一边念叨:“今早大家刚下地,王知青就回知青点忙活了,知道咱淋了两天雨准保冻得慌,特意烧了这锅汤,红糖还是他自己攒的,平时都舍不得吃呢。”另一个妇女接话:“可不是嘛,人家知青心思细,知道咱干着重活,得喝点热的顶顶,比自家兄弟都周到!”
这话一传开,喝着姜汤的人都忍不住夸起来。吴江喝了大半碗,抹了把嘴对身边的林凡说:“王知青确实会疼人,这时候能想到煮姜汤,不容易。”田埂那边,扶着棉花苗的老乡也跟着点头:“这后生实诚,以后有啥难处,咱帮衬着点应该的。”
妇女们提着壶在田埂间穿梭,给水稻田的送完,又往芝麻地走,嘴里的夸赞就没停过。“锅里还多着呢,喝完了再去舀!”张大嫂笑着招呼,看大家喝完姜汤后干劲更足了,自己也觉得心里熨帖——这热汤不光暖了身子,连带着地里的活儿,仿佛都轻快了几分。
严书记正和几个公社干部在田埂上查看排水情况,见张大嫂提着茶壶过来,忙接过搪瓷缸子倒了半碗姜汤。滚烫的甜辣味滑进喉咙,他哈出一口热气,笑着说:“这汤熬得地道,暖到骨头缝里了。”
旁边的武装部干事也喝着汤,接话道:“还是王知青有心,知道大家伙儿淋了雨,特意煮了这个。”严书记点点头,用袖口擦了擦嘴:“说起这王杰,平时看着文文弱弱的,脸色总不大好,听说是有低血糖,干重活都得悠着点。”他顿了顿,望着远处知青们忙碌的身影,又道,“但今儿这事办得敞亮,心思细,能想着地里干活的人,可见也是个顾全大局的好同志。”
另一个干部跟着点头:“可不是嘛,城里来的知青能这么接地气,不容易。这红糖金贵,他肯拿出来给大伙分,就凭这份心,就得高看一眼。”严书记端着茶缸又喝了一口,望着田埂上穿梭送汤的妇女们,嘴角带着笑意:“是块好料子,好好历练历练,错不了。”
王杰还不知道公社的干部们对他的印象改观了呢,不过就是知道也无所谓,毕竟他又不想走行政的路线。想着大家中午回不来,还是整点热乎的饭菜给大家垫垫肚子,做什么好呢?又不能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最后想了想还是打蛇的主意,毕竟此地的大山多,野物也多,附近的猎人也挺多的,借口不就有了。
收拾出两条几斤重的王锦蛇(菜花蛇),从菜地里拔了几根大白萝卜。从空间里取出几块扇子骨切成的碎块,然后是排骨,还有一捆红薯粉,他打算整成地锅炖。先和面,杂酱面整了几斤,和好后,放在面盆里醒发,收拾出几十个小土豆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