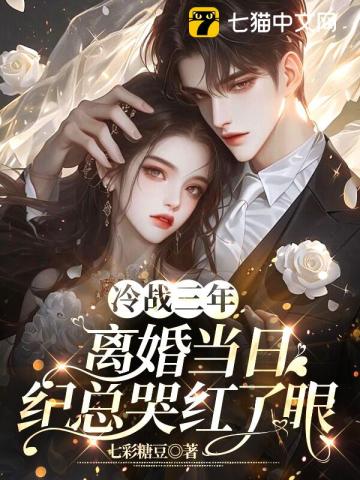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风水云雷电 > 世间的事总是说不清(第2页)
世间的事总是说不清(第2页)
一个多月的时间像指缝里的沙,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梁平的日子过得像上了发条的钟,规律得近乎单调。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出现在林院长的书房,晚上十点被林薇“赶”回客房,中间的十几个小时,不是埋在古籍堆里,就是对着电脑敲论文。
他看了太多书,从宋代的《营造法式》到清代的《相宅经纂》,从晦涩的《周易参同契》到民间抄本的《阳宅十书》,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渐渐爬满了他带来的笔记本。遇到有意思的发现,就立刻整理成论文片段——有时是分析某类符号在不同朝代的演变,有时是考证“风水学说”与古代建筑选址的关联,字里行间全是他独有的认真。
交上去的论文初稿已经堆成了小摞,林院长每次看都忍不住点头,说他“把散落在古籍里的珠子串成了项链”。
研讨室的交流会上,轮到梁平发言时,他总会捧着笔记本站到台前,指着上面的符号和图表,一讲就是半小时。底下坐着的都是名校的教授和研究生,大多研究的是正统建筑学,听他讲“坎卦与水系布局”“震卦对应门窗朝向”,常常面面相觑,眼里带着“这小子在说什么”的茫然。
可梁平自己讲得津津有味,讲到兴头上,还会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起村里姜八能教过的符号,对比古籍里的图案:“你们看,这个‘水纹符’,这里多了一道弯钩,其实是对应‘子水’的方位……”
底下有人偷偷笑,林薇坐在后排,看着他眉飞色舞的样子,也忍不住弯了嘴角——这书呆子,明明知道大家听不懂,却还是像献宝似的,把那些“冷门知识”讲得活灵活现。
散会时,有教授笑着打趣:“小梁啊,你这研究,快赶上咱们林院长年轻时的劲头了,就是……太深奥了点。”
梁平也不恼,挠挠头:“是我没讲清楚,下次我结合建筑实例说,可能好懂些。”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他转身往书房走,脚步轻快,怀里还抱着刚借到的《鲁班经》,仿佛刚才的“听不懂”压根没影响他的兴致。对他来说,能把小时候听来的“胡话”,和古籍里的学问对上号,本身就是件天大的乐事,至于别人懂不懂,反倒没那么重要了。
林薇追上来,递给他一瓶水:“讲得口干舌燥了吧?我爸说你这论文,能填补不少空白呢。”
梁平拧开瓶盖喝了一大口,眼里闪着光:“真的?那太好了!等回去,我得找姜八能老爷子聊聊,他肯定知道更多。”
夕阳透过走廊的窗户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林薇看着他那副“找到宝藏”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一个多月的单调日子,被他过成了独有的热闹。
或许,真正热爱一件事的人,从来不怕孤独。
晓冉对着手机屏幕,手指在对话框上悬了半天,最后还是气鼓鼓地把刚打好的字删了。
屏幕上是梁平半小时前发来的消息,长篇大论讲的是“宋代镇宅符与现代建筑抗震设计的隐性关联”,末尾还附了张古籍截图,问她“你看这个符号像不像上次咱们在博物馆见的瓦当纹饰”。
“像像像,像个大头鬼!”晓冉对着手机小声嘟囔,脸颊气得发红,“学了一个多月,说话越来越听不懂了!每次聊天不是讲符号就是说论文,就不能说句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