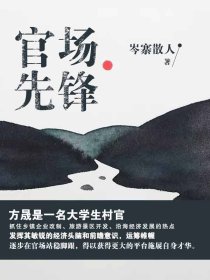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风水云雷电 > 就是很执着(第2页)
就是很执着(第2页)
林薇几乎是疯了一样找梁平。她把两人共事过的设计图翻出来,对着上面标注的每一个勘察地点发呆;想起他说过小时候常去后山看星象,便雇了向导往深山里钻,踩着没膝的积雪找了三天三夜;甚至跑到姜八能老爷子的坟前,蹲在那儿哭了半晌,问老人知不知道他徒弟去了哪儿。
设计院院长——也就是林薇的父亲,被女儿缠得没辙。这位一辈子只信数据和图纸的老工程师,头一回动用了所有积攒的人脉:调监控、查交通记录、托公安系统的老战友协查,甚至联系了地质勘探队,怕梁平是在野外考察时出了意外。三个月下来,他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桌上堆着厚厚一沓排查报告,鬓角的白头发都添了不少。
“这孩子是个搞风水勘察的奇才啊……”老院长不止一次对着空荡的办公室叹气,“真要是没了,国家都得少个能破解古建筑煞气的专家。”
可日子一长,连最开始热心帮忙的同事都渐渐松了劲。有人说梁平怕是卷了项目经费跑路了,有人猜他是不是看破红尘隐居了,议论声慢慢淡下去,就像水滴落入湖面,终会归于平静。
只有林薇没放弃。她对外说要休长假登山旅游,背着个巨大的登山包,跑遍了梁平提过的每一座山、每一个古镇。在黄山的云雾里对着悬崖喊他的名字,在平遥古城的老宅墙上找他可能留下的记号,甚至在某个偏远村落的祠堂里,对着满墙的族谱翻找“梁”姓的痕迹。
晓冉的方式则更安静些。她守着梁平留下的那间堆满古籍的小屋,每天帮他擦拭桌上的龟甲摆件,整理散落的笔记。她托人查了所有与“锁心局”“连山归藏”相关的文献,把查到的线索分类抄在本子上,盼着他哪天突然回来,能立刻用上。偶尔收到林薇发来的定位,她会对着地图研究半晌,在可能的路线上画满密密麻麻的标记。
两个姑娘,一个在明处奔波,一个在暗处梳理,都心照不宣地用自己的方式,守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她们不知道梁平正困在那道结界里,只当他是迷失在了某个角落。
而结界中的梁平,偶尔感知到那两道执着的意念,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疼。他攥紧龟甲,把那点愧疚压下去——只能更快些,再快些,等破了局,再好好补偿这份沉甸甸的牵挂。
林薇在终南山深处已经转了半个月,登山靴磨破了底,脸上晒脱了一层皮。那天暴雨刚过,她踩着湿滑的石阶往上爬,忽然看见崖边的凉亭里坐着个穿青布道袍的老道士,正低头擦拭一把旧罗盘。
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冲过去,声音带着哭腔:“道长,您能帮我算算吗?我找人,一个叫梁平的男人,他……”
老道士抬眼打量她片刻,没接话,只从袖中摸出张泛黄的麻纸,用炭笔寥寥几笔勾了个山势图。图上没标地名,只在一处山坳里点了个红点,旁边画着三道交错的弧线,像三片叠在一起的龟甲。
“顺着溪流走,见着老槐树左拐,三里地外有处断墙。”老道士的声音像山间的泉水,清冽又缥缈,“找不找得到,看缘分。”
林薇接过图纸,手指都在发抖,连声道谢后转身就往山下跑。雨又淅淅沥沥下起来,她把图纸紧紧揣在怀里,生怕打湿了半分。按着老道的指引,果然在山坳里找到一片残垣断壁,断墙根下生着丛野菊,开得正盛。
她绕着断墙走了两圈,忽然看见墙角有块松动的青石板,石板边缘刻着个模糊的“平”字——那是她以前总笑他写不好的名字。林薇的心猛地一跳,蹲下身去搬石板,指尖触到石板的瞬间,一股熟悉的温热感传来,像握着梁平常用的那片龟甲。
石板下是空的,压着半块啃剩的干粮,还有张被雨水洇得发皱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字,是她再熟悉不过的笔迹:“勿念,待破局,自归。”
林薇把那张纸贴在胸口,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砸在青石板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知道,自己找对地方了。他就在附近,他还好着。
雨还在下,她却忽然笑了,抹了把脸,从背包里掏出块新的压缩饼干,轻轻放在石板下,像在完成一个秘密的约定。转身往回走时,脚步轻快了许多——只要知道他在哪,再等多久都值得。
喜欢风水云雷电请大家收藏:()风水云雷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