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光小说汇 > 夜塔集 > 第68章 元旦晚会(第5页)
第68章 元旦晚会(第5页)
心中有个声音在告诉她,只要迈步开始奔跑,就能逃出这片黑暗,逃避那些难堪,尴尬,只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逃避一切。
“跑吧,离开这里吧。”
“不顾一切的跑吧”
“就和那晚一样。”
“告别这些难堪。”
这些声音开始在陈晓的脑中如心魔般环绕着,渐渐盖过了所有声音。
此刻漆黑的舞台就好像她的内心世界一样,台下是外界暗中对她的嘲讽和讥笑,台上是恐惧封闭的她。
“陈晓是不是家境不太好啊。”
“我看她好像都没用过手机。”
“那还用问,前天我跑老师办公室,那贫困生补助名单上有她的名字。”
“嘘,这些话别在人家面前说。”
......
“我怎么从没见过陈晓用洗面奶,洗发水什么的。”
“她好像只会用肥皂。”
“正常,人家那个家庭,能上高中都不错啦。”
这些只是她过往高中生活里的一点点片段。
高中生的歧视并不像中小学那样明显张扬,但像细沙一样无孔不入。
他们不会当面嘲笑,但会在她经过时突然压低说话声音;不会直接说她穷,却总在发新款校服时“不经意”问她要不要换自己的旧衣服:体育课分组时,总有人抢先拉住其他人,留她站在原地等老师安排。
那些关于肥皂和手机的议论像长了脚,从教室溜到走廊,再从食堂飘进宿舍,最后变成所有人默认的“常识”——她当时的处境就像是一块透明玻璃,所有人都看得透她的窘迫,却都默契地假装看不见她的透明。
“是的,也许我当初就不应该上高中,而是接受父亲的安排,去神学院当一名虔诚的教徒。”
陈晓听见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声音,就好像有个看不见的自己在面前和自己讲话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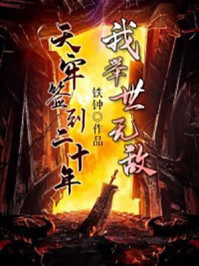
![敛财人生[综].](/qs_html/img/6/6479/6479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