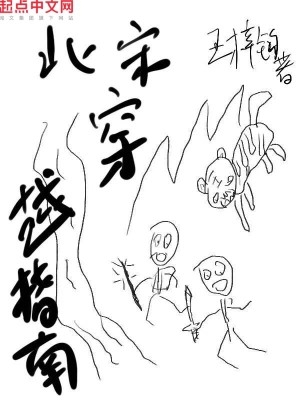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胡沙录 > 第114章 淮水狼烟(第1页)
第114章 淮水狼烟(第1页)
陈五的乌骓在十月初三的晨雾里打了个响鼻,前蹄溅起的泥水沾在他甲叶上,像块没擦净的锈斑。队伍已经在淮河北岸扎营三日,他蹲在土坡上,望着对岸被晨雾裹住的芦苇荡,耳边还响着斥候的汇报:"刘宋前锋离此三十里,王玄谟的步军带着二十辆投石车,后边跟着檀道济的水军 ——"
"放屁!" 陈五把冷硬的胡饼摔在地上,惊得身边的亲兵缩了缩脖子,"檀道济早被刘义隆贬去种桑了,你当我没看过密报?" 他抓起胡饼拍了拍土,塞进嘴里,麦麸扎得嗓子生疼,"再探!把王玄谟的粮道、弩手位置都给我摸清楚!"
亲兵翻身上马时,陈五听见身后传来马蹄声。他回头,看见王慧龙的玄甲骑兵正从东边过来,马背上的旗幡被风扯得猎猎作响,"龙" 字旗角沾着暗红的血 —— 这是他在漠南见过的战旗,当时王慧龙带着八百骑冲散了柔然的右军。
"陈将军!" 王慧龙在十步外勒住马,甲叶撞出脆响。他左脸有道刀疤,从眉骨直贯下颌,是去年守滑台时被刘宋的长戟挑的,"我在南岸截了队南朝斥候,审出王玄谟今晚要渡淮。"
陈五的手指不自觉摸向腰间的陌刀。刀鞘上的牛筋还带着王铁牛的体温,那是出发前连夜换的。"韩延之呢?" 他问,"他的重步兵该到了。"
"在后边。" 王慧龙跳下马,靴底碾过满地的断箭,"司马休之的游骑在西边三十里,说要等咱们布好阵再合兵。" 他从怀里摸出块烤鹿肉,递过去,"吃点热的,夜里要冷。"
陈五接过鹿肉,肉香混着血锈味钻进鼻子。他咬了口,烫得直吸气:"王兄,你这伤......" 他指了指王慧龙的左肩,玄甲下渗出的血把护心镜染成了紫褐色。
"小伤。" 王慧龙扯了扯嘴角,刀疤跟着扭曲,"上个月在悬瓠城,刘宋的弩手射穿了我三层甲。要不是韩延之的铁枪队冲过来,我现在该在洛阳的祠堂里受香火了。" 他蹲下来,用刀尖在地上画着,"淮水这段浅滩多,王玄谟肯定选东边的芦苇荡渡河。咱们把陌刀队摆在滩头,胡骑藏在西边的土丘后,等南朝的步兵过了一半......"
"冲他娘的!" 陈五接口,眼里冒着火,"我带胡骑抄他后队,你和韩延之砍他前军。司马休之的游骑......" 他突然顿住,抬头望向西边,"来了!"
马蹄声像闷雷滚过大地。司马休之的游骑从晨雾里钻出来,马背上的骑士穿着皮甲,腰间挂着环首刀,最前边的骑手披着件黑貂斗篷,正是司马休之。他的马是匹雪青马,四蹄踏在泥里,溅起的水珠在晨光里闪着碎银似的光。
"陈将军!" 司马休之在陈五面前勒马,斗篷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听说你从平城带了三千羽林卫?" 他的声音里带着股子寒,像冬天的洛水,"我司马家的人,最恨南朝的兵 —— 当年刘裕屠我满门,今天我要拿王玄谟的人头祭我叔父!"
陈五注意到他腰间的剑穗是血红色的,穗子上沾着草屑。那是司马家的家传之物,他在太武帝的藏书阁见过记载:"司马氏剑穗,以族中血祭,见血则鸣。" 此刻剑穗无风自动,在马侧扫出个红影。
"司马公。" 陈五抱了抱拳,"今夜王玄谟渡河,咱们的人够么?"
"够。" 王慧龙用刀尖戳了戳地上的图,"我三千玄甲骑,韩延之两千重步兵,你三千羽林卫,司马公八百游骑 —— 共八千七百人。王玄谟的前锋是一万二,后边还有五千水军。" 他抬头,刀疤在晨光里泛着青,"但咱们有淮水天险,有陌刀,有胡骑......" 他突然笑了,"更有陈将军的玄鸟鱼符。"
陈五摸了摸怀里的羊脂玉。那是拓跋清塞给他的,此刻贴着心口,暖得像块活物。他想起昨夜在帐里,王铁牛举着火把,指着地图说:"将军,这滩头的泥地最适合陌刀 —— 南朝的步兵穿重甲,陷进泥里跑都跑不动。"
"传令!" 陈五站起身,甲叶在晨风中撞出清响,"韩延之的重步兵去东边滩头,摆鱼鳞阵!王慧龙的玄甲骑跟我去西边土丘,藏好!司马公的游骑绕到南岸,等南朝的船过了一半,烧他的粮船!"
司马休之的剑穗突然 "唰" 地绷直。他盯着陈五,眼里有火在烧:"烧粮船?好!我司马休之今天就做回火头军!" 他一甩斗篷,拨转马头,游骑跟着他如一阵黑风卷向南方。
王慧龙拍了拍陈五的肩:"我去叫弟兄们备马。" 他转身时,左肩的血又洇湿了甲叶,在地上滴出一串暗红的点。
陈五望着他的背影,突然想起太武帝说过:"王慧龙是晋臣王愉的孙子,当年刘裕杀他全家,他逃到北魏,朕用他不是因为可怜,是因为他比谁都恨南朝。" 此刻他终于明白,那道刀疤里藏的不是伤,是火。
"将军!"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