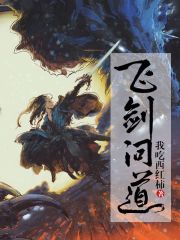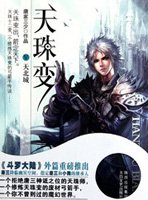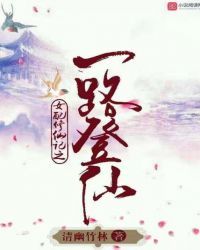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胡沙录 > 第125章 仓廪(第1页)
第125章 仓廪(第1页)
陈五的青骢马踏过田埂时,稻穗正扫着他的靴面。
九月的阳光像化开的蜜,晒得新翻的泥土泛着油光。他翻身下马,蹲在田垄边,指尖掠过沉甸甸的稻穗 —— 颗粒饱满,压得茎秆弯成月牙。田埂上的老农拄着锄头笑,脸上的皱纹里嵌着泥星子:“陈大人,您看这穗子,比去年还沉!”
“王阿公,” 陈五摘了粒稻子放在掌心,“去年亩产三石,今年能有四石?”
“四石五!” 老农拍着大腿,“您教的浸种法、轮作术,比菩萨显灵还管用!” 他指了指远处的晒谷场,十几个娃娃追着麻雀跑,怀里抱着新收的稻穗,“您瞧那小栓子,去年还瘦得像根芦柴棒,现在能扛半袋米了!”
陈五望着小栓子泛红的脸蛋,想起三年前在青禾村 —— 那孩子蹲在墙根啃树皮,肚皮鼓得像吹胀的羊皮袋。他摸了摸腰间的青铜符,符面的云纹被体温焐得温热,像阿史那云的手。“阿公,” 他说,“今年的公粮留足了?”
“留足了!” 老农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抖开是叠田契,“您看,寺里退的三十顷地,我们分了二十顷,留十顷做义田。义仓的米够全村吃半年,连去年涝灾都没动!” 他突然压低声音,“前日里有个游方僧在村口转悠,被我家小子拿扫帚赶跑了。现在谁还信那劳什子佛?我家灶王爷的画像都换了 —— 画的是您和陛下!”
陈五的眼眶热了。他想起灭佛诏颁布那日,太武帝在显德殿摔碎的茶盏;想起智空禅师的鎏金佛像被熔成铜钱时,溅起的铜水像血;想起老张的坟头,今年春天冒出了两株野菊。他站起身,青骢马打了个响鼻,颈上的铜铃叮当作响,惊得晒谷场的娃娃们欢呼着跑过来。
“陈大人!陈大人!” 小栓子举着稻穗扑过来,“我阿娘说,等收完稻子,要给您做糖糕!”
陈五弯腰抱起他,稻穗的清香混着孩子身上的奶味钻进鼻腔。“糖糕要留着给你吃,” 他说,“你吃胖了,阿娘才高兴。” 小栓子的手突然摸到他左腕的刀疤,那是圆觉的木棍砸的,“疼么?”
“不疼。” 陈五摸了摸孩子的头,“这疤是甜的。”
日头偏西时,陈五回到县衙。后堂的案上堆着二十七个郡县的田册,封皮上的朱砂印泥还没干透。他解下外袍,露出左臂缠着的粗布 —— 旧伤虽好了,每逢阴雨天还会抽痛。小李端着茶进来,右手的断指已经结了痂,端茶时手腕微微发颤:“大人,这是王二婶送的新茶,说比去年的香。”
“搁这儿。” 陈五翻开第一本田册,“江州的寺田退了九千顷,均给了一万三千户;冀州的普济寺拆了,木料盖了八所村学……” 他的手指停在 “代郡” 那页,“代郡的法藏寺?不是说全拆了么?”
“回大人,” 小李凑过来,“法藏寺的主持圆寂前留了份遗嘱,说要把剩下的二十顷地捐作义田。县尉说,那老和尚临终前念了首诗,什么‘佛在田间,不在庙堂’。”
陈五笑了。他想起法藏寺自焚那日,焦黑的尸体旁滚着个铜磬;想起普济寺的年轻和尚还俗后,教老和尚扶犁的模样。他摸出支狼毫笔,在 “代郡” 页边批了行小字:“义田立碑,刻‘魏民同耕’。”
“大人,” 小李欲言又止,“昨夜巡城时,在西市逮了个形迹可疑的人。他怀里揣着张崔府的旧帖,还骂您是‘灭佛的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