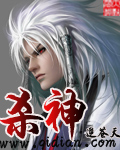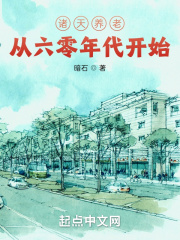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胡沙录 > 第161章 元服血刃(第1页)
第161章 元服血刃(第1页)
陈五站在显德殿廊下,望着檐角垂落的冰棱,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腰间短刀的 “守” 字。太武帝的龙案上堆着半人高的奏疏,最上面是鸿胪寺的折子 —— 南朝刘宋派了使团,说是要来贺新帝加元服,可陈五闻着,那墨香里混着股子腥气,像极了三年前崔峻书房里的沉水香。
“大人,陛下醒了。” 王福捧着铜盆从偏殿出来,盆里的热水腾着白雾,“今早用了半碗小米粥,还说要跟着您学批折子。”
陈五转身,见八岁的拓跋弘正扒着殿门往外瞧,小身板裹在玄色小朝服里,像只缩在壳里的乌鸫。他走过去,弯腰替孩子理了理垂落的绶带:“陛下今日要学的,是看奏疏里的谎。” 他指着龙案上的鸿胪寺折子,“南朝说使团带了二十车贺礼,可淮河入冬早,他们的船半个月前就该到了,怎么现在才递牌子?”
拓跋弘歪着脑袋,手指戳了戳折子上的朱印:“陈卿是说,他们在拖时间?”
“陛下聪明。” 陈五摸出怀里的甜灯,金砂在掌心慢慢聚成 “危” 字,“拖到加元服那天,拖到平城的雪封了雁门关。” 他抬头,见王福正盯着殿外的铜鹤灯,灯芯烧得噼啪响,“王公公,去查查鸿胪寺当值的典客,尤其是那个上个月刚从扬州调过来的。”
王福的喉结动了动,躬身退下。陈五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三天前在崔府密室找到的账本 —— 最后一页记着 “扬州典客,银千两”。甜灯在袖中发烫,他知道,这 “危” 字不是冲他来的,是冲龙椅上那个攥着玉扳指的孩子。
“陈卿,” 拓跋弘突然拽他的衣角,“阿翁的扳指,我昨晚梦见他了。他说... 说加元服那天要穿红里子的吉服,别冻着。”
陈五蹲下来,看见孩子眼底的青影 —— 这半个月,崔家余党闹得凶,小皇帝总在半夜惊醒。他解下自己的狐裘,裹在孩子身上:“陛下放心,臣让人把紫宸殿的地龙烧得旺旺的,红里子吉服也让尚衣局赶制了三套。” 他指了指殿外的雪,“等仪式完了,臣带您去看冰灯,甜市的老艺人雕了只玄鸟,翅膀会动。”
拓跋弘的眼睛亮了,刚要说话,殿外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李昭裹着染雪的皮裘冲进来,刀疤被冻得发紫:“大人!云中急报!山胡残部联合南朝的私兵,昨夜劫了咱们的运粮队,三十车粟米全烧了!” 他从怀里掏出截焦黑的布片,“这是从火场里捡的,上面的云纹,和崔家祠堂的幔子一样。”
陈五的指节捏得发白。他想起上个月周铁的密信,说云中郡的戍卒里混进了生面孔,操着吴语骂娘。甜灯在掌心炸开,金砂凝成 “火” 字,和三年前太仓失火时一模一样。
“周铁呢?” 他问。
“周将军带雁门军追出去了。” 李昭抹了把脸上的雪,“但山胡人熟悉地形,怕是要往漠北跑。末将请命,带玄甲军去接应!”
陈五摇头:“玄甲军留在平城。” 他抽出星枢刀,刀身映着李昭的脸,“崔家的余党要的是乱,乱了朝局,乱了陛下的加元服。南朝的使团、山胡的劫粮,都是幌子,他们真正的刀,藏在平城的雪底下。”
李昭的瞳孔缩了缩:“大人是说... 刺杀?”
陈五没答话。他望着拓跋弘,孩子正趴在龙案上画玄鸟,笔尖在纸上戳出个洞。殿外的更鼓敲过午时三刻,王福捧着个檀木匣进来,匣里是尚衣局新制的吉服,金线绣的玄鸟振翅欲飞。
“大人,” 王福压低声音,“鸿胪寺的典客张九,今早让人送了幅画到崔府旧宅。末将让人跟着,那宅子的地窖里藏着二十口箱子,箱子里全是三棱弩。”
陈五的手搭在星枢刀上,刀鞘的牛皮磨得发亮。他想起昨夜在御书房翻的《大魏律》,谋逆者当诛九族,可崔峻的孙子还在敦煌戍边,那孩子今年才七岁,该是在雪地里捡骆驼粪烧火。
“王福,” 他说,“去传旨:加元服仪式提前到明日卯时。尚衣局、光禄寺、太常寺,今夜不许合眼。” 他又对李昭道,“带玄甲军把崔府旧宅围了,人要活的,箱子要全的。”
李昭领命而去。陈五转身,见拓跋弘正盯着他腰间的短刀:“陈卿的刀,是不是又要见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