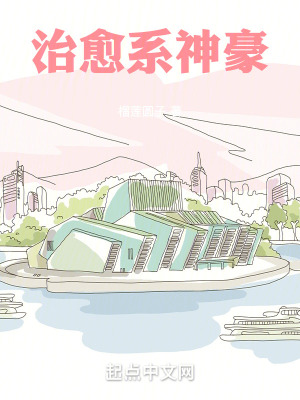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招财进我 > 招财进我 第113节(第5页)
招财进我 第113节(第5页)
陶竹不想让他看见她哭,怕他又瞎贫。
她从浅尝辄止的啄吻改为温柔绵长的深吻,忽地,蒋俞白唇瓣上一片濡湿,是她伸舌头了。
蒋俞白揽着她的后腰,声音很低,像是用气声在问:“不疼了?”
她刚才“飞”出来的那一下动作之迅猛,想一想也知道是没什么事了,他翻过身,把她压在身下。
这个姿势,又是很容易看到哭过的眼睛,陶竹没犹豫,把脖颈往上抬了一下。
蒋俞白没看见她的眼睛,倒是把她颈间清晰的曲线看了一清二楚,他拇指顺着她的脖颈一路延下轻轻摩挲,鼻尖蹭着她的脸颊,一下一下,吻的勾火。
她的身体禁不起逗,没几下,就软的像是一滩温水,情迷意乱间,两人四目相对。
蒋俞白的眼神里一直有种睥睨众生的傲气在,此时此刻掺杂着掩不去的欲,声音哑的不行,没放在她的手,但动作停了:“哭了?”
他没等到她的回答,只见她上半身微微上仰,他以为她是要抱她,谁知道他是轻轻咬了下他的喉结。
又疼又痒。
身体里原始放肆就这样被勾起来。
蒋俞白没换睡衣,身上还穿着婚礼上穿过的白衬衫,被他扯得七零八落,丢在一边。
昏昧的小灯亮在头顶,房顶上倒映着两道交缠在一起的身影,陶竹抱着他的腰,嘴唇贴在他的唇上:“说你爱我吧。”
她不是一个沉溺于甜言蜜语里的人,但说不清道不明的,很想听他说。
“我爱你。”蒋俞白没犹豫,他的鼻尖蹭在她的脸颊上,发出沉重的喘息声,咬字却还是清晰的,“我爱你。”
昨天陶竹的反应太痛苦了,蒋俞白是真的没发挥好。
今天的情况明显是不一样的,她跟蒋俞白在一起,一次又一次。
已经不知道折腾到几点才睡过去,只知道床单上,沙发上,西洋钟前,遍布了黏腻的乳白水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