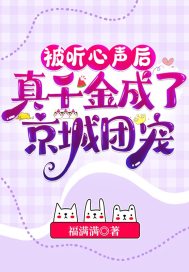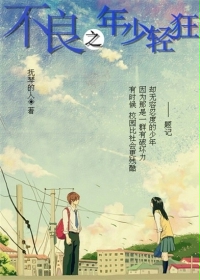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浮生重启录 > 第3章 青年失意痛(第2页)
第3章 青年失意痛(第2页)
而他正忙着修订《捐官则例》,给那些用银子买官的富商定品级。
我这才明白,当年我们在国子监里读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早被他们换成了“先官场之利而利”。
我曾在国子监的碑刻里见过刘大人年轻时的名字——那时他是太学生刘仲文,在“谏官言事碑”旁题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他中进士后被派往扬州盐运司,首月便因查获三船私盐触怒盐商。
那夜他被绑在运河边的柳树上,三十大板下去,脊骨发出碎裂声。
盐运使王大人撑着油纸伞来看他,靴底碾过他咳出的血沫:“刘贤侄,这扬州的盐,是朝廷的命脉,也是你我的命脉。”
半月后,他娶了王大人的独女,婚房的红绸下,藏着盐商送来的“贺礼”——二十道盖着户部关防的浮引勘合。
他曾在洞房夜对着铜镜揭开创口,看见血痂下新生的肉,像极了盐引上的朱砂印。
从那以后,他靴底总沾着盐粒,袖口总藏着“浮引勘合”。
如今他案头的《盐法考成》,某页用朱笔圈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旁边是他批注的小字:“非吾愿,实乃官场漕规耳。”
更痛的是婉娘。
那年扬州的三月三,她在瘦西湖的诗会上吟“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鬓边的海棠簪子随声轻颤。
我当时正被盐商刁难,那盐商非说我的诗稿抄袭,要我当众道歉。
她却拨开人群,将一锭银子拍在桌上:“这位先生的诗稿,我买了。”
后来才知道,她是扬州最大的盐商之女,却偏偏爱往书斋跑——她父亲的账房里,锁着一摞摞《盐引勘合》,每道勘合都对应着上千引官盐,而她的绣房里,却藏着我送她的《杜工部集》,书页间夹着她抄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她父亲第一次见我时,正坐在铺着波斯地毯的客厅里数银票。
他上下打量我洗得发白的青衫,嘴角撇成个鄙夷的弧度:“魏举人?呵,举人能换几担盐?”
后来我做了扬州同知,他依旧瞧不上我,说我“芝麻官,难登大雅之堂”——直到我因整顿盐政被弹劾,他竟在宴会上拍手称快:“我就说嘛,寒门出不了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