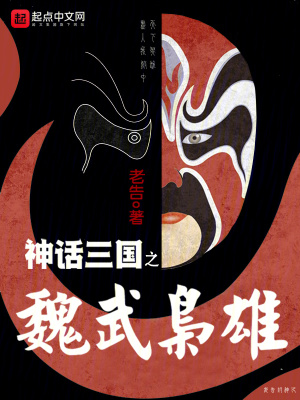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墨香策山河 > 第78章 我陪着你(第2页)
第78章 我陪着你(第2页)
潘令宁走出清风楼之时,风雪已停,荼白的苍穹竟还微微放晴,暖光映着白雪,亮堂得刺目。
她已手背遮挡视线,试着远眺厚重云层中,依然透出强光的阳乌,眼泪倏忽滚落,可脸上却获得了些许的暖融融。
耳边忽然响起一声召唤:“潘掌柜,你出来了?快上马车,外头凉!”
她低头擦拭泪痕,适应了稍许,才看到齐远已在马车内招手等候着了。
潘令宁赶紧上了马车,齐远又细心把暖炉奉给她,并且左右拾掇,给她盖上厚褥,以驱散腿脚的寒意,同时询问:“她答应了吗?”
“答应了。”
“如此甚好!那我抓紧功夫,再多写几阙词,隽才兄说道,还有几位友人也愿意加入我们,为鬼樊楼一案创作诗词,以及在士林中设法传阅,往后,不止是闺阃女子,便是士林文人也将广而告之,趁此大朝会,万国来朝之机,必将轰动朝野!”
“多谢你,齐公子!”
他这么做,也是冒了杀头的大罪,潘令宁利用了他的赤诚之心,可也隐隐愧疚和担心。
齐远却乐呵呵:“你不必谢我!巾帼怀仁尚叩天,七尺举义忍旁观?我反而该替这世道,谢谢你!”
“敢怀仁义叩天问公道者,无分男女,又岂止是七尺二郎的责任?”
“娘子所言极是,叩天问道不该只归于男女责任,是齐某狭隘了!只是某仍旧有些担心,消息放出去了,哪怕北契国使团接住,他们果真上钩?”
“齐公子,北契国使团今年来朝队伍十分隆重,皆为贵族宗室、文官要员,你可知为何?”
“我只听闻了些许风声,他们不满五年前的纳金额度,企图议讨增加岁输!”
“看来齐公子也听说了,我这些日子,依托当时送纸攀结的人缘几经打听,得知契国使团不满足五年前南廷西伐失败,约定北输乞合的四十万岁银,想增至六十万,否额仍旧侵扰边境,鼓动党项人独立。”
“岂有此理!真当我们南廷只能软弱服膺,偏安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