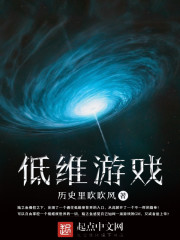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墨香策山河 > 第136章 独当一面(第1页)
第136章 独当一面(第1页)
潘令宁点了一下头,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崔相公可是等我用膳?”潘令宁看着一桌子菜,她早已饥肠辘辘,主动问起。
崔题点头:“劳碌了一天,你也饿了吧?快坐下来吃饭吧!”
潘令宁也不再客气,依言入座,而后主动给崔题盛了一碗汤。
崔题看她一双纤纤玉手捧过瓷碗,腕见一双玉镯白糯油润,飘着乳黄花云,成色上佳,价值不菲。
她在京中这段时间鲜少打扮自己,更遑论佩戴价值连城的饰物,如今她从歙州回来,衣着也鲜亮了,鬓发间也多了几件饰物,手中更戴着和田玉双镯。
想来这镯子也可能是她母亲留下来的,她回歙州之后,把家中惯用的物品、父母兄长留下的旧物,其他重要的东西都打包了行李,足足五车辎重,一同带来京城了。
“你的行李,都放在老槐巷的庭院?往后都要住在老槐巷?”崔题思及至此,便也顺势一问。
潘令宁点了点头,双手捧着汤碗置在他眼前:“崔相公请喝汤,我明日便雇人上门来把漪月居的私人旧物,都搬到老槐巷去了。这些日子,委实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
“这般着急?”崔题轻喃道,只觉得她回来之后,比之从前,与他更疏离了几分?
“不算着急,早该如此了!”潘令宁双手垂落在桌下,眼帘亦低垂,酝酿片刻之后,极其郑重地望着他道,“我不想一直寄人篱下,不论是阿蛮家,还是崔相公的汲云堂,亦或者齐物书舍,皆是不得已而暂居的庇护所,可如今潘家也只剩了我,我若想重振家业必需得独当一面,而不可如初入京师,仍旧只能依赖于旁人的力量!
“更何况我日后与崔相公同路同行,共襄讲义堂,难道也还只能一直寄居汲云堂,仰望着崔相公?我不想着崔相公一直把我看成借势攀援的凌霄花,而是当成可并肩而立之人!”
“宁儿,你又怎知,我还是以曾经的眼光看待你?”
“不管你如何看待我,我看待我自己,亦需以新的眼光。当初我父亲仅为潘家的第三子,不受重视,他凭一己之力成为‘万金侯’,撑起了潘家的一片天地,母亲早年也多受父亲的宠爱,日子过得富贵清闲,父亲走后她对抗数伯族亲,和蠢蠢欲动的掌柜,亦独当一面。母亲撒手人家,我也一直在哥哥的庇护中无忧无虑不问家中事,可如今,潘家也只剩了我,我亦需得自立成长,独当一面,我不过完成潘家每一代接班人的使命!”
崔题听罢,心下惊讶,他总算明白了她回来之后,为何变得不一样了,原来她已自发蜕变成为潘家的接班人,而她身上传承的一直是父母兄长的品质。
他早该知道眼前的女子,不是他初见时的不谙世事的娇养深闺的金丝雀,单纯懵懂、不谙世事是她的茧,而她身为凭一己之力创造落雁纸成为万金侯的潘怀的女儿,她又怎么只是金丝雀?当破茧之后,她必将化蝶!
听闻她搬出的理由之后,崔题心下稍安,至少她不是因他的缘故,才不喜住在汲云堂,反而,她存着与他并肩而立的志向。
至少他在她心中,是追逐的标杆,他在她心里有一定的分量!
崔题微微勾起了嘴角,言语便愈加温柔:“宁儿是打算,往后便在京城立业,而不再回歙州?听闻李青回禀,你在歙州,除却保留老宅,庄铺田产皆任由叔伯打理?”他说罢又微微蹙眉,他也不知此为好事还是坏事,难道她甘心把父亲基业拱手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