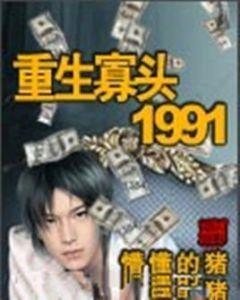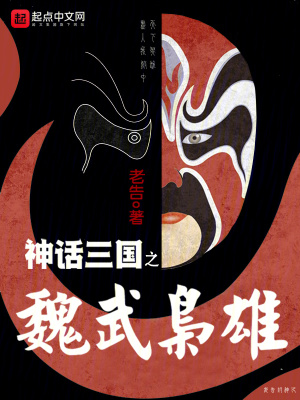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八尾传奇之空宅记 > 第10章(第1页)
第10章(第1页)
>
“莫非后来不曾寻到?”
“不错,活生生的一个人,竟从此便不再现世,真真是怪相。州府也多次派下官儿来追查,衙门内各个人等都遭提审了一遍,那几个贴身近侍更是夹棍板子轮番吃一遭,然而也说不出个四五六来。”
“那后来如何?”
郝三叹道:“还能如何,官人们要交差,自然拘了三个近侍回州府去看押,说是等大理寺再审。不过有两个走到半路上病亡了。此事便不了了之。”
那姓罗的老衙役接着道:“旁人也不知道那三个近侍冤是不是冤的,然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终无法定罪,剩下那个便关在州府牢里拖着了。之后陆续有官人到永安,住进这县衙便有些不太平。我记得跟着来的仿佛是孙承宗孙官人,到任不过两月,便得了头痛之症,无药可医,丢了性命;再后来是张官人,大名却不记得了,仿佛是去东山题诗,却摔断了骨头,站不起来,于是告假养伤去了;再后来……还有几个人?”
郝三见他捏了指头计数,不由得笑道:“老哥哥昏了,后面还有五六个,只不过名姓都记不太清了。”
五德道:“那么死在这县衙内的官人有几位?”
郝三也掐指一算,道:“倒是很有五六位哩!病故的不少,有得头痛的,有中了暑热的,有吐血而亡的……不过有一位却是跌落在荷花塘中给淹死的。”
五德道:“看来这县衙果然是邪气得紧。这许多年来,莫非竟未找懂风水的断上一断?”
郝三低声道:“陈主簿请人来此,却未看出什么来,却说这宅子修的方位大吉大利呢!我却不信!”
五德道:“既如此,新官人暂不住此地才是!”
“咱都这么说,陈主簿本给新官人准备了别处落脚,新官人却推了,真真是少不经事。”
另一差役笑道:“却也难说!这位张官人是新科状元,文曲星下凡,福气大了,定能压服住此地的邪气。”
郝三道:“那便阿弥陀佛了!可新官人上任便死了这许多人,竟好似带了灾来的!”
他刚说完,又自觉失言,轻轻扇了自己一个嘴巴:“老蠢物胡言乱语,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