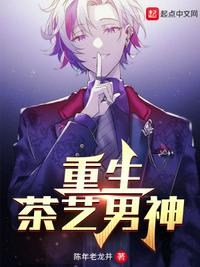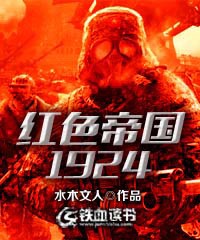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无冬之春(西幻NP) > chapter89最佳听众(第3页)
chapter89最佳听众(第3页)
不过他很友善,且可以包容朋友因迟钝而产生的不同意见。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温情,瓦尔特利会满足辛西娅的绝大部分要求,即便他很难理解,也会装点洞穴,尽力让他的朋友获得更舒适的生活。
毕竟谦逊和友善是他最大的美德,他的博学都需要排在这两项后面。
然而辛西娅很快意识到,瓦尔特利的友善和谦逊背后,潜藏着一个足以吞噬任何凡人理智的无底洞——他那永不枯竭、毫无边界的分享欲。
这种分享欲,远超辛西娅作为吟游诗人所能理解的任何形式的交流或倾诉。
它不是对话,而是单方面的、裹挟着金属粉尘和巨大声浪的信息泥石流,日以继夜、永不停歇地冲刷着她脆弱的神经。
瓦尔特利不需要深思熟虑的回应,但他极度渴望——或者说要求即时反馈。
一个眼神的飘忽、一次迟了半拍的点头,都会引来他关切的询问:“哦!我亲爱的辛西娅!你是否对这个关于沙虫肠道菌群多样性的观点感到困惑?让我再详细解释一遍……”
或者:“哈!你也觉得那个地精的笑话很妙对吧?我再来一个!”
辛西娅被迫进化出了生存本能——一套高度自动化的“嗯嗯嗯系统”。
她的喉咙发出恰到好处的升调“嗯?”表示疑问,降调“嗯。”表示理解,短促的“哈!”
配合僵硬的笑容表示被逗乐,以及漫长、空洞的“嗯……”表示正在深度思考。
她的灵魂常常飘在洞穴顶部,冷漠地看着自己的躯壳在丝绸堆上尽职尽责地扮演一个会呼吸的点头娃娃。
而瓦尔特利对分享的细节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
描述一只路过的甲虫,他不仅要精确到它有几条腿、哪条腿的关节处有一小块斑点——他认为那是“命运的烙印”,还执着于推测它的虫生目标、模仿它爬行时沙粒发出的细响——并即兴用低沉的嗡鸣模仿了一段。
最后他还会为这只甲虫虚构一个横跨沙漠寻找失散伴侣的悲情故事。
辛西娅觉得自己的大脑像一块吸满了水的海绵,再也塞不进一丝关于甲虫的信息,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瓦尔特利用热情的口水继续将它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