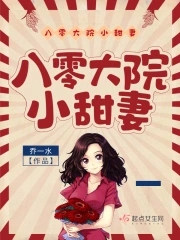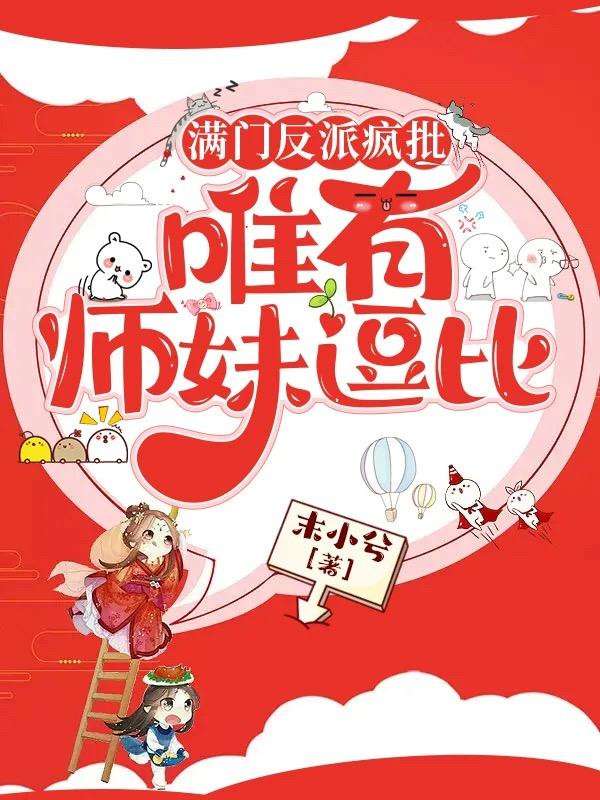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大明:朱重八的六岁小皇叔 > 第207章 朱五六的野心(第1页)
第207章 朱五六的野心(第1页)
朱五六站在城楼上,望着九州光网如活物般脉动,忽然握紧了手中的竹笛。
笛身上新生成的光纹正与北斗星的轨迹呼应,仿佛在指引他望向更远的天地。
“系统,若将这文脉共振推向四夷,会怎样?”他轻声问。
玄铁令牌立刻投射出星图,原本局限于中原的光网边缘,正有细碎的光丝试图向西域延伸,却在玉门关外寸寸消散。
“异域文明有其自身频率,强行共振只会引发湮灭。”系统的声音带着警示,“譬如波斯的祆教圣火,其‘二元论’频率与‘中庸’相悖;罗马的法典光纹,运行逻辑与‘礼’的脉络难以兼容。”
朱五六却想起曲江池的鱼。那些鳞片上的光纹并非天生,而是文脉觉醒后逐渐生成的共振印记。
他转身走向鸿胪寺,那里正停着一艘刚从扶桑返航的遣唐使船,船帆上还沾着东海的盐粒,在月光下泛着银光。
“把这个挂在桅杆上。”他将一枚刻着“和而不同”的铜铃递给船长。铜铃接触船帆的瞬间,立刻渗出与“海纳百川”频率相合的青光,顺着帆布的经纬蔓延。
“下次返航时,告诉我扶桑的樱花,是否会在绽放时唱出《诗经》的调子。”
三个月后,遣唐使带回的消息令人振奋。
据说铜铃在航程中始终发出清越的声响,每当船经某处海域,浪花便会在船尾拼出当地渔民的祷词,其中既有“风平浪静”的汉字光纹,也有扶桑语“海の神”的假名波动。
最奇的是抵达港口时,当地工匠打造的漆器上,突然浮现出“巧夺天工”的光流,与铜铃的频率产生了微弱共鸣。
“这便是‘求同存异’的力量。”朱五六站在西市的货栈里,望着那些从波斯运来的地毯。
织毯上的葡萄纹样间,正有细小的光丝与长安酒肆的“丰年”频率相触,如同初萌的枝芽试探着伸展。
他指尖轻触毯面,玄铁令牌立刻浮现出新的文字:“文明共振非同化,乃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