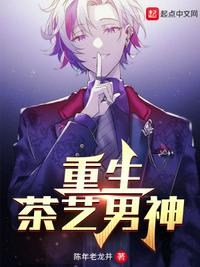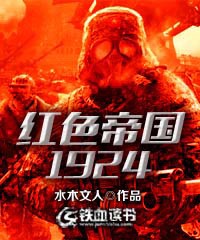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选英雄改变历史?等等,我先逝逝 > 第199章 车驾临边营,芍陂验真章(第1页)
第199章 车驾临边营,芍陂验真章(第1页)
元嘉二十八年秋七月廿三,宋文帝刘义隆的车驾抵达芍陂北岸时,晨雾尚未散尽。
皇帝身着常服,披着件玄色披风,在侍臣搀扶下走下马车,鞋履踩在湿润的泥土上,发出 “噗嗤” 声响。
不远处,一片连绵的二季稻田在晨风中起伏,稻穗沉甸甸的,几乎垂到地面。
田垄间,身着短褐的百姓与披甲的兵卒并肩劳作,锄头与镰刀的碰撞声,混着粗豪的山歌,在芍陂水面上回荡。
辛弃疾接到消息出营迎接,见到皇帝亲自前来,也是颇为意外。
“辛爱卿,” 刘义隆握住辛弃疾的手,语气恳切,“朕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
辛弃疾躬身道:“陛下言重了。为国尽忠,乃臣之本分。些许流言蜚语,臣并未放在心上。”
刘义隆看着眼前这位年轻将领,眼中满是赞赏与愧疚:“爱卿的《九议》,朕已反复研读,字字珠玑,皆是安邦定国之策。之前是朕糊涂,险些中了北魏的奸计。从今往后,淮河防线,便全仰仗爱卿了。”
“臣定不负陛下所托!” 辛弃疾沉声应道。
“陛下,” 辛弃疾身着戎装,大步迎上,甲叶上还沾着昨夜巡营的露水,“臣已备下轻车,可载陛下巡视屯田与敌台。”
文帝摆摆手,目光落在田埂上一堆新收的稻穗上,稻粒饱满如珠,在晨光中泛着油光:“不必乘车,朕想走走看看。辛爱卿,这就是你说的‘每亩三石’一年两熟的稻谷?”
“正是,陛下。” 辛弃疾蹲下身,抓起一把稻穗,指腹碾过谷粒,“此乃臣从南方引入的‘占城稻’,耐旱早熟,又经冶山铁肥滋养,故得此丰收。”
他指向远处的灌溉渠,“芍陂之水,已按《考工记》之法疏浚,可自流灌溉万亩良田。”
文帝弯腰,捡起一枚掉在地上的稻穗,指尖触到谷壳的粗糙纹理,忽然咳嗽起来,侍臣连忙递上锦帕。
辛弃疾见状,示意随从捧来一盏热粥:“陛下,此乃芍陂新稻所煮,臣斗胆请陛下品尝。”
文帝从侍膳太监那里接过了瓷碗,热气氤氲中,粥香醇厚。
他尝了一口,米粒软烂,带着自然的甘甜,不禁点头:“好粥。辛爱卿,你这屯田,不仅是屯粮,更是为我大宋屯民心啊。”
“陛下圣明。” 辛弃疾肃容道,“臣以为,固边之本,不在坚城利甲,而在民心归附。”
“《荀子·哀公》有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今百姓入敌台,战时为兵,平时为农,既得温饱,又受庇护,自然肯为朝廷效死。”
说话间,一阵急促的梆子声从远处敌台传来。辛弃疾侧耳听了听,笑道:“是‘五星连珠’烽烟,示警有小股敌军袭扰。陛下可随臣上敌台观阵。”
登上濉口一座敌台顶层,文帝扶着垛口喘息,眼前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