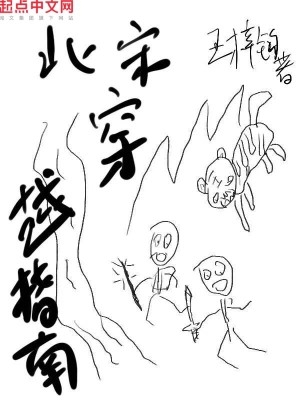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枝上韫浓 > 第131章 别选孩子,选我(第2页)
第131章 别选孩子,选我(第2页)
太医令今日本就要照例前来请平安脉。
元韫浓在软榻上伸出手腕,太医令搭上她的脉搏,凝神细诊。
裴令仪坐在一旁,看太医令的眉头越皱越紧,愈发紧张。
元韫浓的脉象似乎让太医令困惑,他换了另一只手,再次凝神感受,脸色变幻不定。
他猛地抬头看向元韫浓,眼神充满了震惊和惶恐。
“殿下……”太医令收回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臣斗胆请再仔细诊一次殿下的脉象……”
元韫浓被他反应惊得一愣,皱了皱眉,“脉象如何?直说无妨。”
裴令仪厉声道:“说!到底如何?”
太医令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冷汗涔涔,“滑……滑脉,殿下这是喜脉啊!”
犹如惊雷落下。
“喜脉”二字令裴令仪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一阵苍白。
犹如被老天狠狠嘲弄一样,喜脉?怎么可能是喜脉?
这怎么可能!
元韫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放在膝上的手缓慢地覆在了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之上,带有一丝不可置信。
跟前世一样,千防万防,都没有防住的孩子。
太医令战战兢兢地跪在不远处,“回禀陛下,臣以项上人头担保,此确是滑脉无疑,胎息虽初萌尚微弱,然脉象圆滑如珠,往来流利,此乃天佑大裴!天佑……”
“闭嘴!”裴令仪猛地打断了他。
元韫浓多久没从裴令仪身上看到这种暴戾了?
因为更多时候她远比裴令仪脾气更坏,又或者说是裴令仪在她面前装得太好了。
裴令仪死死盯着跪伏在地的太医令,“滑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