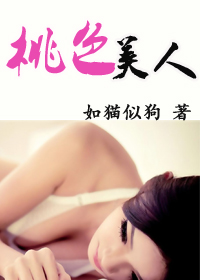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二战那些事儿 > 第65章 明斯克的口袋(第3页)
第65章 明斯克的口袋(第3页)
GKO的成立,标志着苏联的权力结构,在战争的极端压力下,完成了从和平时期的“集体领导”向战时“个人高度集权专政”的彻底转变。斯大林通过GKO这个机构,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地集中到了自己手中,成为了整个苏联战时体制的绝对核心和最高主宰。
在讨论成立GKO的会议上,面对当时极其严峻的军事形势和斯大林本人在战争初期一度出现的“消沉”状态,党内高层(比如莫洛托夫自己或者其他人)可能也曾有过一些其他的想法或建议,比如是不是可以暂时让莫洛托夫(作为政府首脑)来主持大局,或者成立一个更具“集体领导”色彩的战时委员会。但这些想法,都被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当场拒绝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分享或挑战他的最高权力,尤其是在这国家危亡的时刻,他更需要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起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指挥这场战争。
在完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后,斯大林还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沉默太久了。
自6月22日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长达十一天未发表任何公开声明。这种“沉默”,一度在社会上引发混乱和不安。在7月3日,沉默终于被打破。斯大林通过广播发表了他亲自撰写并审定的战时第一次全国讲话。
那一天,苏联千百万收音机前的人民,第一次听到这个习惯以“同志们”自称的统帅,突然换了一个开场白——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陆海军的战士们!”
这种称呼,在苏联宣传中是极不寻常的。它不仅突破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语言范式,更触动了普通百姓最本能的民族情感。“兄弟姐妹们”,那是一种家庭式的召唤,是当故土面临灭顶之灾时的血脉唤醒。
在这篇讲话中,斯大林首次正式将这场战争命名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呼吁全民团结,进行全面抵抗与焦土政策,并鼓励在被占区组织游击战。他承认苏联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强调“我们必须保卫每一寸苏联的土地,不惜一切代价!”
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语言和诉求发生了深刻转变。这次讲话不仅有对希特勒与纳粹的猛烈谴责,也夹杂着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东正教色彩,它不再局限于抽象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诉诸于“保卫祖国”“扞卫人民”“反抗外辱”的本能情感。这一宣传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让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人都找到了共同战斗的理由。
因为此刻,“共产主义”或许还不足以让人赴死,但“家国”可以。
从组织上看,GKO的强权集中为战争体制提供了钢铁般的执行力;而从精神动员上看,7月3日的讲话则为全社会注入了灵魂。这套政治—宣传的双重机制,是苏联能够在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逐步组织起反攻力量的根本保障。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就在苏联西方面军在比亚韦斯托克和明斯克地区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同时,苏联在外交和战略态势上的处境,也变得更加险恶。那些在战前与苏联有过节、或者对苏联领土抱有野心的邻国们,一看“红色巨人”似乎要不行了,也纷纷跳了出来,想趁火打劫,捞取好处。
苏芬战争的耻辱,芬兰人可一天都没忘记。当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传来时,芬兰政府虽然一开始在外交上还比较谨慎,宣称保持中立。但实际上,他们早就跟德国人暗通款曲,允许德国军队利用芬兰北部的领土作为进攻苏联摩尔曼斯克方向的基地。
1941年6月25日,当德国空军的飞机(有些可能就是从芬兰机场起飞的)开始轰炸列宁格勒等苏联城市时,苏联空军也对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等城市进行了报复性的空袭。这一下,芬兰政府找到了“借口”!心里想着可算能报仇了,他们立刻宣布,苏联对芬兰发动了无端攻击,芬兰被迫进入“继续战争”状态,(以保卫国家主权和收复在冬季战争中失去的领土!)
6月26日,芬兰正式向苏联宣战,加入了德国一方,从卡累利阿地峡和东卡累利阿地区向苏军发动了进攻。芬兰军队的加入,使得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在进攻列宁格勒时,得到了重要的战略策应,也使得列宁格勒面临着来自南北两面的夹击。
在外交辞令上,芬兰人也玩得挺溜。他们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德国的“盟友”,只是与苏联单独进行一场“继续战争”,目的是“自卫”和“收复失地”,并不是要参与到德国称霸欧洲的侵略计划中去。这种说法,当然是自欺欺人,但在当时也确实迷惑了一些西方国家。
南边的罗马尼亚,在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独裁统治下,更是德国忠实的仆从国。罗马尼亚对在1940年被苏联强占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一直耿耿于怀。德国入侵苏联,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