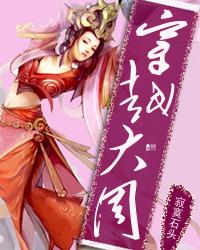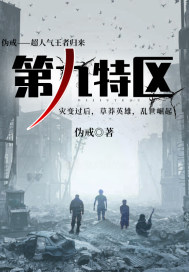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二战那些事儿 > 第100章 风沙尽头是阿拉曼(第1页)
第100章 风沙尽头是阿拉曼(第1页)
咱们上一回说到,图卜鲁格再度陷落,三万英联邦士兵举手投降,丘吉尔在华盛顿的雪茄差点掉进咖啡里;而隆美尔这边,刚摘下元帅权杖,正踌躇满志地挥师东进,一路“沙漠狂飙”直扑埃及门户!
从昔兰尼加到马特鲁,英军是一路丢盔卸甲、仓皇败退;开罗街头风声鹤唳,连英军司令部都开始琢磨要不要预备把苏伊士运河给炸了。眼看着这只“沙漠之狐”就要咬住帝国的咽喉,一场生死决战,正在埃及西部那道最后的防线——阿拉曼,悄然酝酿。
北非的沙漠,在经历了1942年初那场短暂的、充满了火药味的寂静之后,终于要迎来一场更大规模、也更具决定性意义的“钢铁碰撞”了。这一次,战场的名字,将永远与“转折”二字联系在一起。
加查拉战役的胜利,像一针强效兴奋剂,打进了隆美尔和他的德意志非洲军团的血管里。虽然他手底下的兵力在之前的战斗中也损失不小,坦克数量更是少得可怜(估计连意大利人的通心粉都快供应不上了),但胜利的喜悦,往往能让人暂时忘记疲劳和饥饿。一些德军将领的头脑,已经被沙漠的烈日和胜利的幻觉给冲昏了,觉得英国人不堪一击,开罗和苏伊士运河,简直就像是摆在餐桌上的烤火鸡,伸伸手就能拿到。
隆美尔本人,虽然比他手下那些咋咋呼呼的军官要清醒一些,但也难免自信心爆棚。他看着地图上那条通往尼罗河三角洲的虚线,仿佛已经看到了他的装甲部队在金字塔下耀武扬威的景象。一个大胆的、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构想,开始在他脑海中成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必须乘胜追击,直取开罗,夺下苏伊士运河!让英国人彻底滚出非洲!”
于是,在占领了图卜鲁格(这座倒霉的城市,在短短几个月内又一次易手,简直成了双方拉锯的“共享单车”)之后,隆美尔不顾后勤补给已经濒临极限的危险,指挥着他那支由德国精锐和意大利“凑数部队”组成的混合军团,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向着埃及腹地,开始了新一轮的、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具赌博性质的一次“闪电东进”!
德军的推进速度,在初期确实是惊人的。溃败的英国第八集团军,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只能节节败退,把一座又一座的城镇和据点,拱手让给了追击的德军。马特鲁、福卡……这些曾经的英军防御支撑点,在隆美尔的装甲矛头面前,如同纸糊的一般,一捅就破。
英军的补给线,虽然随着战线的东移而大大缩短,理论上应该更通畅了。但问题是,部队的士气已经跌到了谷底,指挥系统也乱成了一锅粥,情报部门更是频频出错,经常是“隆美尔的坦克都快开到司令部门口了,情报员还在报告说敌军在一百公里之外喝咖啡呢”。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有再多的补给,也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战斗力。
然而,隆美尔这位“沙漠之狐”,心里也清楚得很,他现在玩的,就是一场“空城计”加“心理战”。他的非洲军团,经过加查拉战役的消耗,早已是强弩之末,坦克和车辆的油料,很多时候都得依靠缴获英军的补给来维持,简直是“吃着敌人的饭,砸着敌人的锅”。他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把所有的筹码都押在了这最后一搏上,希望能在英国人反应过来、重新组织起有效防御之前,一鼓作气冲到苏伊士运河边。他知道,一旦他的攻势受挫,补给线被切断,那他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必将陷入弹尽粮绝、四面楚歌的绝境,到时候别说饮马尼罗河了,恐怕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了。
更让隆美尔窝火的是,就在他拼了老命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时候,远在柏林和罗马的最高统帅部,却像是集体得了“健忘症”一样,并没有及时地向他提供足够的兵员、装备和油料支援。希特勒的注意力,可能还主要集中在东线那无底洞般的苏德战场上;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呢?估计还在为他的“新罗马帝国”梦游呢,指望他能给隆美尔送来什么有用的东西,那还不如指望沙漠里长出西瓜来得实在。后勤补给的瓶颈,就像一根无形的绞索,开始越勒越紧,悄悄地扼住了隆美尔前进的咽喉。
阿拉曼之地:天然防线的选择
就在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挟着加查拉大捷的余威,像一股黄色的沙尘暴一样席卷埃及西部沙漠,兵锋直指亚历山大港和开罗的时候,英国第八集团军的残部,总算是在一个名叫“阿拉曼”的地方,暂时停住了溃败的脚步。
这个阿拉曼,在地图上看起来,只是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一个不起眼的小火车站。但它的地理位置,却像老天爷专门为打防御战量身定做的一样,简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然要塞!
您瞅瞅这地形:阿拉曼地区的北面,是波涛汹涌的地中海,海军的舰炮可以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虽然英国海军在地中海也挺忙的,得防着德国人的U艇和意大利人的舰队);而南面呢,则是一片广阔无垠、几乎无法通行的巨大盐沼地——卡塔拉洼地。这洼地,地势低洼,流沙遍地,坦克和车辆一旦陷进去,就跟掉进了无底洞一样,根本别想爬出来,简直是装甲部队的“天然坟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从地中海边的阿拉曼,到卡塔拉洼地的边缘,这中间的防御地带,宽度只有大约60公里!这在广阔无垠的北非沙漠战场上,简直就是一道窄得不能再窄的“瓶颈”了!英军只要在这条狭长的走廊上,构筑起几道纵深配置的防御阵地,部署上足够数量的反坦克炮、地雷和铁丝网,就能有效地阻止隆美尔的装甲部队从两翼迂回包抄,迫使他们不得不从正面硬攻!这对于兵力已经捉襟见肘、又极度依赖机动作战的隆美尔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东英军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在加查拉惨败之后,深知局势的极端危险。他没有像有些指挥官那样,在失败面前惊慌失措,或者把责任推给下属。他果断地解除了第八集团军司令里奇中将的职务(这位将军也确实是“压力山大,能力有限”),由他自己,亲自接管了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权!而且,他还一改之前那种习惯于在开罗的司令部里遥控指挥的“官僚作风”,直接把自己的指挥部搬到了阿拉曼前线的一个简陋的地堡里,与士兵们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准备在这条最后的防线上,与隆美尔进行一场决定生死的较量。
奥金莱克的这一举动,虽然有点“悲壮”的意味,但在当时那种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的情况下,无疑是给濒临崩溃的第八集团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士兵们一看,连总司令都跑到前线来跟咱们一起啃沙子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抄家伙,跟德国佬拼了!
于是,在阿拉曼这条最后的防线上,一场戏剧性的对比,开始悄然上演:一边,是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带着他那支虽然疲惫不堪但依然凶悍善战的非洲军团(以及那些士气时好时坏的意大利“盟友”),挟着连战连捷的余威,高歌猛进,试图一鼓作气,突破英军的最后屏障,直捣黄龙;另一边,则是临危受命、孤注一掷的奥金莱克将军,指挥着那些刚刚从溃败中重新集结起来的、缺兵少将、装备也残缺不全的英联邦部队,在这片狭窄的沙漠走廊上,布下了一道道用血肉和钢铁铸成的“铁墙”,准备与侵略者进行最后的殊死搏斗。阿拉曼,这片在埃及艳后时代可能还默默无闻的荒凉之地,即将因为这场关乎帝国命运的血战,而永远载入世界战争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