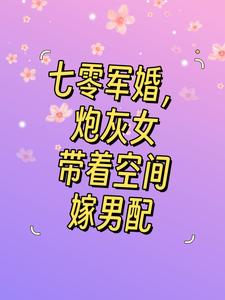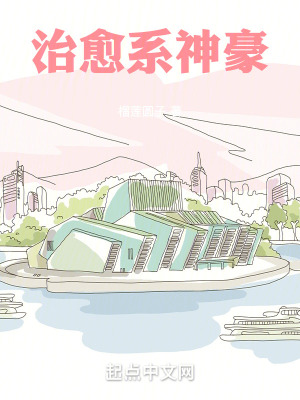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二战那些事儿 > 第113章 面子战役(第2页)
第113章 面子战役(第2页)
一切的开端,似乎都有些莫名其妙。“蓝色方案”的战略核心本是直取高加索地区的油田,以维系帝国的战争机器。占领斯大林格勒,最初只是为了切断伏尔加河运输、保护主攻方向侧翼的次要目标。但战役打着打着,这个次要目标却匪夷所思地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当战事进入白热化,双方几乎都杀红了眼,如同两个在赌桌上输光了筹码却不肯离场的赌徒,死死地盯着对方,嘴里反复念叨着:“我还没输!”
要探究这其中的缘由,很大一部分,或许只能怪这个城市的名字——斯大林格勒。这使得一场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两位最高统帅之间的个人对决。希特勒寄望于用德军的铁蹄,将斯大林的“脸面”按在伏尔加河的泥地里摩擦;而斯大林,则绝不能容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被法西斯所玷污。于是,一场宏大的战役,被简化为一场关乎个人荣辱的、你死我活的“面子战争”。
要理解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狂热,我们必须深入两位主角——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内心,因为他们共享着一个本质身份:独裁者。之前说过,独裁者统治的根基,并非来自民众的授权,而是源于其精心构建的“神话”。他必须让民众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归、永远正确的“神”。神在打仗,是不可能失败的。一旦承认失败,哪怕只是战术性撤退,都会让神话出现裂痕,民众会猛然惊觉:“原来你也是个会犯错的普通人!”这种对统治根基的动摇,是任何独裁者都绝对无法容忍的。
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格勒的军事意义早已退居其次。它成了一场两位领袖都绝对输不起的政治豪赌。至于伤亡多少、损失多大,在那至高无上的“面子”面前,似乎都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代价。
这也解释了为何当将军们苦苦哀求撤退时,希特勒会暴跳如雷。在他看来,“撤退”就等同于“失败”,等同于他“神话”的破产。
可为什么他就是听不进那些理性的、关乎军事存亡的利害分析呢?
一部分原因,自然是他作为一个前一战“陆军下士”的军事局限性。指望希特勒对现代战争的战略纵深和作战节奏有天才般的理解,确实是强人所难。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独裁者与将领之间,天然存在着“公司老板”与“项目总监”般的结构性不信任。
我们将第三帝国视为一家公司,希特勒是创始人兼老板,而曼施坦因、古德里安这样的将领,则是高级项目总监。
项目总监(将领们)的核心目标,是让自己的项目(战役)取得成功。他们想建功立业,想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他们会基于数据和经验提出方案,但他们不必为整个公司的生死存亡负终极责任。项目失败,大不了降职或被解雇,可以去“另一家公司”(在历史中虽不可能,但风险承担的层级是类似的)。
老板(希特勒)则完全不同。他必须从全局考虑,平衡各个项目,担忧公司的“资金链”(战略资源)、“总人力”(兵员),以及最重要的——公司的生死存亡。一旦公司破产(战争失败),他将失去一切。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这种目标、视野和风险承担上的根本不一致,注定了“老板”希特勒对他的“项目总监”们无法完全信任。他会怀疑,这些经理人是不是为了自己的业绩和方便,而损害了公司的长远利益?是不是缺乏与公司共存亡的忠诚?
所以,斯大林格勒的悲剧链条就此形成:一个次要军事目标,因其名字而被“老板”升级为关乎“公司形象”和“个人面子”的头号工程。当“项目总监们”基于专业判断,报告项目已陷入绝境、建议止损时,“老板”的第一反应不是分析数据,而是怀疑经理们的忠诚与能力。最终,这位多疑、自负且对军事一知半解的“老板”,固执地推翻了所有专业意见,亲自下场“指手画脚”,将公司最宝贵的资产(第六集团军),全部投入到这个注定要烂尾的“面子工程”中,直至其轰然倒塌。
而可怜的保卢斯就成了希特勒“面子工程”的牺牲品。
希特勒要求保卢斯自杀,是这场灾难性“面子工程”彻底失败后,“老板”为了挽回自身“面子”、强行控制项目结局叙事、并试图将一场耻辱的溃败扭曲为“英雄史诗”的最后,也是最冷酷的一步。
这背后,是“老板”希特勒在项目彻底崩盘后的危机公关和企业文化重塑,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1. 强行更改项目结局:从“项目失败”到“项目献祭”
一个项目的结局有两种。一种是提交一份“失败报告”,承认亏损,清算资产。另一种,则是举办一场悲壮的“献祭仪式”,告诉所有人,这个项目不是失败了,而是为了公司更伟大的愿景,光荣地牺牲了。
投降 = “项目失败报告”: 保卢斯如果投降,就等于他这个“项目总监”签署了一份官方的、不可辩驳的“失败报告”。这份报告会明确写着:由于“老板”的灾难性决策,导致项目组全体人员被俘,设备全部丢失。这是一个冰冷的、充满数据和事实的、无法洗白的商业失败案例。
自杀 = “项目献祭仪式”: 但如果保卢斯自杀,故事就完全变了。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就可以立刻发动,将结局描绘成:“我们伟大的项目总监,在弹尽粮绝后,为了扞卫公司的荣誉,选择了与项目共存亡!这是一场光荣的、为理想献身的英雄壮举!” 这样一来,一场耻辱的失败,就被扭曲成了一场可以激励后人、凝聚“企业向心力”的悲壮献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