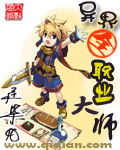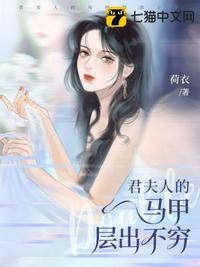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二战那些事儿 > 第115章 最后的荣耀(第2页)
第115章 最后的荣耀(第2页)
第三步:反击。当时机成熟时,南北两支装甲集群同时发动闪电般的钳形攻势,一举切断苏军突出部的根部,将其主力合围、击溃在第聂伯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广阔地带。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然而,希特勒仍旧迟疑。他不仅天然地不信任“撤退”这个词,更不愿在政治上承受主动放弃哈尔科夫的巨大压力。他一度质疑曼施坦因的判断,认为这是胆怯与“妥协主义”的表现。
但希特勒不能否认两件事:第一,曼施坦因的战略判断,在之前的克里米亚和斯大林格勒外围解围战中,都已被证明是惊人地准确;第二,敌人的坦克,已经逼近他现在正落脚的这个机场,扎波罗热本身也不再安全。
历史,最终由残酷的军事现实,击败了偏执的意识形态意志。
在战术理智和切身安全的双重压力下,希特勒终于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勉强同意了曼施坦因的“反手一击”方案,并破例签署了一份授权令:授予曼施坦因元帅对南方集团军群的战役级行动指挥自由权——这在希特勒越来越喜欢“遥控指挥”的战争后期,是极其罕见的。他的语气仍旧冰冷而生硬,不甘心地对曼施坦因说:
“我希望你,不会像他们(指斯大林格勒的将领们)一样懦弱地败退。”
曼施坦因没有反驳,只是沉默地回敬了一个标准的普鲁士军礼。他知道,他为自己,也为整个南方集团军群,赢得了最后一次主动创造战机的机会。
曼施坦因的反手一击(2月19日 – 3月6日)
希特勒的专机刚刚飞走,曼施泰因的指挥棒便开始以惊人的效率挥舞起来。
兵力部署:德军的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在霍特和克莱斯特的指挥下,开始秘密地向预定的反击出发阵地集结。而由保罗·豪塞尔指挥的党卫军装甲军(下辖“警卫旗队”、“帝国”和“骷髅”这三个王牌师),则被作为最锋利的矛头。
苏军的茫然:对面的苏军,无论是瓦图京的西南方面军,还是戈利科夫的沃罗涅日方面军,都还沉浸在收复哈尔科夫的胜利喜悦之中。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张由德军装甲部队编织的死亡之网,已经悄然张开。
攻势展开:2月19日,德军的反击正式开始!豪塞尔的党卫军装甲军,如同出鞘的利刃,从南翼猛地插向苏军波波夫机动集群的侧后方。德军的坦克,利用其在火力和战术上的优势,迅速地截断了苏军的联络线和补给线。
苏军的反应:瓦图京在接到侧翼告急的电报后,大惊失色。他急忙命令他手中已经疲惫不堪、油弹两缺的第3坦克集团军等部队掉头,去堵塞那个巨大的缺口。结果,这些早已是强弩之末的苏军坦克,一头撞上了以逸待劳、装备精良的党卫军装甲矛头。
溃败:战斗的结果,几乎是一边倒的。苏军的波波夫机动集群和第6集团军(此第6集团军为苏军新建,非斯大林格勒被围者)被彻底击溃,第3坦克集团军也遭受重创。曼施泰因的反击,不仅成功地稳住了濒临崩溃的南线战局,更反过来将苏军的进攻部队打得是落花流水。北线罗科索夫斯基原本准备对中央集团军群发动的攻势,也因为南线的急剧恶化而被中途叫停。一场战役上的大逆转,就这样发生了。
哈尔科夫血战(3月11日 – 3月15日)
在击溃了苏军的野战机动兵团之后,曼施泰因的原计划,是绕过哈尔科夫,从其北面渡过顿涅茨河,将苏军的残部合围。然而,党卫军的指挥官豪塞尔,这位政治动机浓厚、渴望为“斯大林格勒复仇”的纳粹悍将,却公然违抗了曼施泰因的命令!
豪塞尔的违令:3月7日,豪塞尔不顾曼施泰因“避免巷战、保存实力”的指令,执意指挥他的党卫军装甲军,对哈尔科夫市区发动了猛烈的强攻。
惨烈的巷战:“警卫旗队”和“帝国”师的装甲掷弹兵,与苏军的守备部队,在哈尔科夫的街头巷尾,展开了极其惨烈的逐屋争夺。市中心的捷尔任斯基广场、巨大的拖拉机厂区、以及哈尔科夫火车站等要地,反复易手。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在了这片乌克兰的土地上。
占领与复仇:3月14日,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德军终于宣布完全控制了哈尔科夫。为了炫耀武功,党卫军狂妄地将市中心的广场,更名为“警卫旗队广场”。紧接着,一场针对伤兵和所谓“游击队员”的血腥报复开始了。党卫军冲进医院,屠杀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苏军伤兵,并纵火焚烧了大量的建筑物,声称这是为“斯大林格勒死难的战友复仇”。
就这样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以苏军的失败而告终,双方开始形成对峙状态。这场战役也成为了双方指挥官命运的又一个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