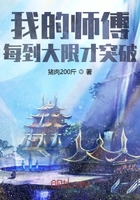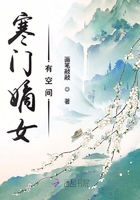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二战那些事儿 > 第129章 绝地营救(第1页)
第129章 绝地营救(第1页)
上一回咱们说到,盟军的“哈士奇”虽然拆家成功,在西西里岛上插上了星条旗和米字旗,但过程却磕磕绊绊,充满了各种“乌龙”和“内卷”,最后还让德军的主力,在眼皮子底下溜之大吉,留下了一个“不完美的胜利”。
然而,西西里岛的陷落,像一颗投入地中海的深水炸弹,其引发的政治海啸,却远比军事上的胜负,来得更猛烈,也更具戏剧性。这场海啸的中心,不在柏林,不在伦敦,也不在华盛顿,而在那座永恒之城——罗马。风暴的中心,则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却众叛亲离的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
1943年7月25日,罗马的夏夜,闷热而又充满了不祥的气息。
就在这一天,统治了意大利长达二十一年之久的“领袖”墨索里尼,在参加完一次气氛诡异的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之后,被他的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三世召进了王宫。等待他的,不是嘉奖和安慰,而是一纸冰冷的解职令。紧接着,这位曾经让整个意大利为之疯狂的独裁者,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被一群宪兵“客气地”请上了一辆救护车,从此,人间蒸发。
消息传到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正在地图前为东线战局焦头烂额的阿道夫·希特勒,当场就炸了!他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在作战室里来回踱步,咆哮着,将手中能拿到的一切东西都狠狠地摔在地上。
“叛徒!一群卑鄙无耻的叛徒!”他对着他那些噤若寒蝉的将军们嘶吼,“他们竟然敢背叛我!背叛我们共同的事业!墨索里尼,我最好的朋友,我唯一的盟友,竟然被这群懦夫给关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更是对我们整个法西斯事业的背叛!”
据说,在最初的暴怒之后,希特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叼着雪茄,凝望着窗外那片阴郁的森林,用一种近乎梦呓的语调,对身边的秘书说道:“墨索里尼的倒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文明世界对抗布尔什维克洪流的最后一道盾牌……现在,这面盾牌,碎了。”
在这位德国元首看来,墨索里尼的倒台,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虽然经常拖后腿但至少在政治上还算“铁杆”)盟友那么简单。这其中,交织着复杂的面子问题、战略考量和意识形态上的唇亡齿寒。
面子:作为法西斯主义的“老大哥”,墨索里尼的倒台,无疑是给了纳粹德国一记响亮的耳光,严重打击了轴心国阵营的士气。
战略:意大利一旦“反水”,那德国在整个地中海的南翼,将彻底门户洞开,盟军可以随时从意大利这个“跳板”登陆欧洲大陆,直接威胁到德国的腹地。
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希特勒需要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他自己的国民证明,法西斯的“兄弟情谊”是牢不可破的,他绝不会抛弃自己的盟友。
于是,一个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希特勒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斩钉截铁的语气,下达了下去:“找到他!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不,他必须活着回来!”
被推翻的墨索里尼,此刻正经历着他人生中最灰暗、也最屈辱的一段旅程。
由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的意大利新政府,为了防止他被德国人救走,或者被国内的法西斯余孽找到,像对待一件“烫手的山芋”一样,将他秘密地在各个偏远的、与世隔绝的地方,来回转移。
他先是被一艘军舰,带到了那不勒斯湾外一个名叫“蓬扎岛”的小岛上,关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每天对着窗外那片蔚蓝但又充满了绝望的地中海发呆。
没过几天,为了安全,他又被一架水上飞机,秘密地转移到了撒丁岛东北角一个更偏僻的、名叫“马达莱纳岛”的海军基地。
可即便是这样,意大利新政府还是觉得不放心。最终,他们决定,把这个“麻烦的囚徒”,送到一个绝对安全、也绝对与世隔绝的地方——那就是位于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大萨索山顶上的一家高山滑雪酒店,帝国将军酒店。
这酒店,海拔高达2100多米,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缆车索道与外界相连。冬天,这里是滑雪胜地;夏天,这里则是与世隔绝的“天空之城”。意大利人觉得,把墨索里尼藏在这里,那简直是万无一失,德国人就算长了翅膀,也别想飞上来。
墨索里尼,这位曾经在罗马的阳台上,对着成千上万狂热民众挥手致意的“领袖”,如今,却成了一个被囚禁在山巅之上的、孤独的囚徒。他每天能做的,只有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或者隔着窗户,凝望着远方那连绵不绝的、如同监狱围墙般的山峦。通信被完全隔绝,看守他的宪兵,也是一批换了一批,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绝望之中,他在自己的日记中,用颤抖的笔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里,不是酒店,这是一个元首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