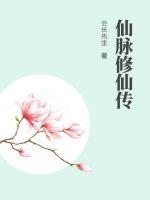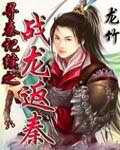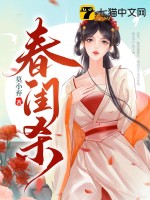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浮生重启录 > 第2章 洛城初见芜(第2页)
第2章 洛城初见芜(第2页)
可她们说,上个月的赈济,被衙役以“磨耗折损”为由,扣得只剩小半碗。
县衙比我想象的更破败。
三间瓦房的屋檐塌了一角,用几根歪脖子木头支着,“明镜高悬”的匾额斜挂着,“明”字的“日”部落了块漆,倒像是“月镜高悬”,透着股阴森。
门柱上贴着张新告示,是前任李大人走时贴的“禁革陋规”,可墨迹未干就被人用泥糊了,露出“……驿站不得苛索百姓……”的字样——典史王顺后来告诉我,李大人走时,驿站的马夫们凑钱给他送了“万民伞”,伞面上绣的却是“刮地三尺”四个隐字。
典史王顺带着两个衙役迎出来时,我看着他的公服洗得发白,补钉用的竟是粗麻布,揖还没作完,袖口的线头就挂在了门框的铁钉上,扯出的布纹里露出半片褪色的绣字——那是崇祯年间的“忠勇”二字,他慌忙用手掌掩住,说“是上任知县赏的号衣。”
“大人……您可算来了。”
王顺的声音嘶哑,眼圈发黑,从袖筒里摸出个油纸包,“这是前任李大人留下的《钱粮账簿》,您瞧瞧吧。”
账簿的封皮写着“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洛城县收支”,可翻开第一页,“地丁银”项下就用红笔打了个叉,旁边注着:“奉抚台批,悉数解送藩库,作河工银。”
再往后翻,“赈灾粮”栏里画着个大大的空仓,仓角写着行小字:“半仓陈谷,已被巡检司刘大人提走充作'剿匪军粮',有领状在案。”
跟着王顺走进正堂,地上的方砖缺了几块,露出下面的黄土,踩上去能感觉到细细的沙粒硌脚。
一个衙役正趴在桌上写什么,走近一看,竟是用树枝在沙土上画押,旁边放着一本破旧的账册,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有些地方还被虫蛀出了洞。
账册里夹着张残破的《催科票》,票上写着“欠银三钱四分”,画着的锁链图案已被指腹磨平——那是去年百姓交不上税时,衙役用来吓唬人的“欠粮锁票”,按《赋役全书》,灾年本可缓征,可巡检司的批文下来,却是“照常征解,逾期加罚”。
后院的西厢房是我的卧房,一张瘸腿的木板床,墙角结着蛛网,窗纸上的破洞用稻草堵着,风一吹,稻草就发出簌簌的声响。
我放下行囊,腰间的玉佩碰到桌角,发出一声清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