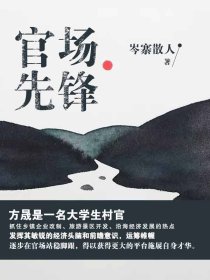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朕那失忆的白月光 作者:吉利丁 > 第292章(第1页)
第292章(第1页)
他呼吸平稳,神色安静,垂首整理药材,似乎没有注意她和别人的交往,比上昨天更是正常了些。
看起来她带着他出去一圈还是有用的。
还未到正午,雨就噼里啪啦地下了起来,密密麻麻,倾盆如注,砸在药坊檐下,响得震耳。
雨大得几乎能与那日她罚卫昭站在外头的暴雨相提并论,只是这回,他没再被丢出去,而是站在她身边。
韩玉堂果然冒雨来了,一脚踏进门,披着湿透的蓑衣,衣角还滴着水。头发贴在脸侧,像只在泥里滚了一遭的公鸭。
“奴才来给陛下、娘娘回话。”
他躬身作揖,语气殷勤,“昨儿开下的方子极好,奴才娘亲身子缓过来了些,大抵就是寻常高热,吃了一副就不烧了。娘娘这手艺,妙手回春呐!”
他笑得满面谄媚,卫昭在一旁,头也没抬一下,只将一捆杜虫端正地放回木屉。
钟薏想到他们明日要走,不经意提议:“若身子还是不稳,就不必赶行程。让她多养些日子,你们先走。”
她去看卫昭。
男人终于抬起头,目光落在她脸上,露出一个温顺的笑:“都听漪漪的。”
韩玉堂千恩万谢,提着钟薏又给他娘开的药包离开。
身影还未消失,两名年轻的书生撑着伞匆匆躲雨进来,带着一身湿气,鞋底踩在地砖上发出“哒哒”的声响。
她原本没抬头,可却听得一人低声道:“我听说这病是昨日爆发的,咳了血,一下倒了七八个人,不知真假。”
另一人压低声音:“真事,我亲戚就在那,说整条街都封了,县衙请了大夫都挡不住,听说缺人手,病人都排到巷子口了。”
“源头呢?有没有查?”
“哪查得过来?他们县官话都不敢多说,说是风热邪气,十有八九是压下来了。”
钟薏手中笔顿了一下,眉心微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