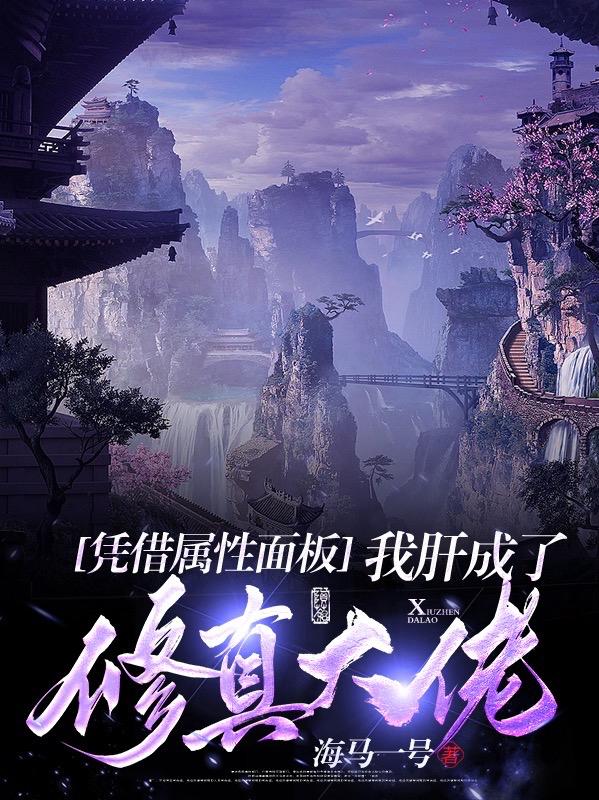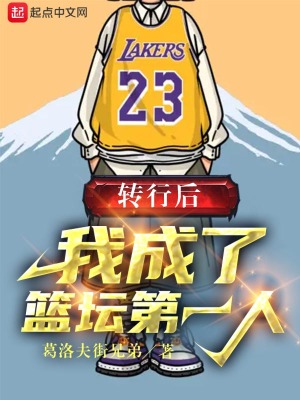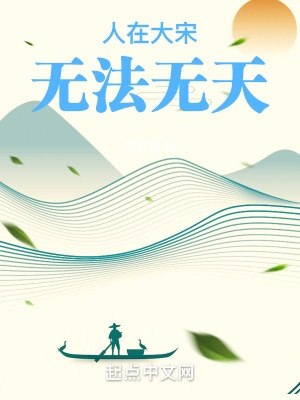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大明,我来了! > 第47章 浊浪淘清官(第1页)
第47章 浊浪淘清官(第1页)
第二天拂晓,天边刚泛起一丝鱼肚白,徐恭一行已收拾妥当,他们没有惊动任何人,如同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河督行辕那片简陋的泥屋。
徐恭并未去开封府城,而是调转马头,带着人,一头扎进了黄河下游更广阔的千里河滩。
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可他还是需要更多的证据。
在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一处偏僻的河工物料临时堆场。
一个满脸风霜的老河工,正哆哆嗦嗦着给徐恭指认着堆料场上几垛明显比别处稀少许多的芦苇席。
“……大人……小的……小的不敢乱说……”老河工的声音压得极低,几乎被大风吞没。
“说。”徐恭的声音不高,却让老河工不寒而栗。
老河工猛地一颤,下意识地左右张望了一下,才凑近一步,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是……是管库的赵书办……他……他让小的们报账的时候……按十成报……可实际……实际只领了七成的席子……那……那三成的银子……小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他浑浊的眼中满是恐惧:“大人……您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赵书办……他……他跟府衙的……”
徐恭面无表情,只是对身后一名校尉使了个眼色。
那名校尉会意,立刻上前,从怀里掏出一本册子,翻到其中一页,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归德府某次支取“加固堤身芦席十万领”的条目。
徐恭的目光在那册子、老河工惊恐的脸、以及眼前这明显不足数的芦席之间,冷冷地逡巡了一个来回。
“民夫的工钱和口粮呢?”徐恭又问。
“这…这,小老儿就不清楚了,那是粮吏他们管的事,我只负责看守料场。”老河工急道。
……
在淮安府(今江苏淮安)一段刚刚完成加固的堤坝下。
徐恭一身寻常商旅打扮,带着一个同样乔装的校尉,像是路过歇脚。
一个面黄肌瘦、裹着破棉袄的中年河工,正蹲在堤脚处啃着硬邦邦的杂粮窝头。徐恭“不经意”地坐到他旁边,递过去一个装着温热烧饼的油纸包。
“老哥,辛苦了,你是河工?”徐恭的声音刻意放缓,带着一口“南直隶”口音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