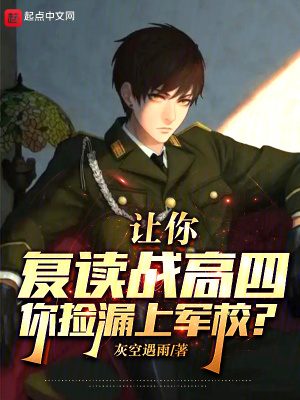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二战那些事儿 > 第77章 北上还是南下(第3页)
第77章 北上还是南下(第3页)
而对于苏军来说,张鼓峰事件虽然打退了日本的挑衅,但也确实暴露了远东部队在大清洗后战斗力有所下降的问题。这让斯大林对远东的防务更加重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柳赫尔元帅这位在张鼓峰事件中指挥苏军取得胜利的功臣,回国后不久,因为指挥不利导致损失过大的罪名,在1938年10月底被秘密逮捕,并在11月初就惨死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之中,据说是受尽酷刑折磨而死。由于布柳赫尔在国内和军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斯大林甚至不敢公开指控他,更不敢立即宣布他死亡的消息,他的死讯直到很久以后才被逐渐披露。一位战功赫赫的元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这无疑是大清洗恐怖政策的又一铁证,也让红军内部的寒意更深了一层。
至于有人说说“图们江出海口划给苏联”,这个说法在历史上并不准确。图们江的下游是中、朝、俄三国的界河,苏联在沿海地区本身就拥有出海口。张鼓峰事件主要是围绕着陆地边界的争议,并没有导致图们江出海权的变更。但这场冲突无疑进一步巩固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加深了其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我们说的外蒙古)的控制和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说它为日后外蒙古最终在苏联支持下实现“独立”(脱离中国)埋下伏笔,倒也有一定的道理。
诺门罕战役(哈拉哈河战役):精锐尽没的“绞肉机”与731部队的“首秀” (1939年春夏)
如果说张鼓峰事件只是给日本陆军敲了下警钟,让他们知道苏联这头“北极熊”的爪子还是挺锋利的,那么紧随其后的诺门罕战役,则彻底打断了“北进派”的脊梁骨,让他们真正尝到了与苏联红军正规部队大规模交战的惨痛滋味!
1939年5月至9月,在外蒙古和伪满洲国的边境地区,一个名叫诺门罕(蒙古语,靠近哈拉哈河)的不毛之地,日本关东军(主要是其精锐的第23师团,由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指挥,以及部分第7师团和伪满洲国“兴安军”的部队)与苏蒙联军(由后来的苏联名将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指挥,当时他还只是个军级指挥员)之间,爆发了一场持续数月之久、规模空前(在当时日苏之间是这样)、也极其残酷血腥的边境战争。
这场仗的起因,跟张鼓峰事件差不多,也是因为一块有争议的边界地区。但这次,双方投入的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远超张鼓峰。日本关东军那帮少壮派军官,在张鼓峰吃了点小亏,心里一直不服气,总想找机会把场子找回来,也想进一步试探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实力和战争决心。
他们一开始还是老套路,觉得凭着“皇军”的“武士道精神”和“万岁冲锋”的“优良传统”,一定能把那些“赤色毛熊”打得落花流水。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次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张鼓峰时期可能还受到大清洗影响、指挥有些混乱的苏军,而是由朱可夫这样一位深谙现代大兵团合成作战之道的“战神”精心调教和指挥的、装备了大量坦克(包括BT系列快速坦克,其性能远超日军的“豆战车”)、重炮和飞机的苏联红军正规部队!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朱可夫的指挥,那叫一个“稳、准、狠”!他先是利用日军初期的骄狂和轻敌,诱敌深入,在哈拉哈河东岸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消耗日军的锐气和补给。然后,他秘密地从后方调集了强大的预备队,包括数个坦克旅和摩托化步兵师,以及大量的炮兵和航空兵部队。
到了8月下旬,朱可夫觉得时机成熟,一声令下,苏蒙联军在空地一体的密切协同作战下,对突入哈拉哈河西岸的日军主力(主要是第23师团)发动了毁灭性的钳形攻势!苏军的坦克集群像铁犁一样,反复冲击和碾压日军的步兵阵地;苏军的炮兵火力也远比日军猛烈和精准,几乎是将日军的阵地犁了一遍又一遍;苏军的飞机更是牢牢掌握着制空权,对日军的地面部队、炮兵阵地和后勤补给线进行着不间断的轰炸和扫射。
而日本陆军呢?他们的坦克(主要是八九式中战车和九五式轻战车)在苏军的BT坦克面前,简直就像纸糊的一样,一打就穿;他们的反坦克武器也根本对付不了苏军的坦克集群;他们的步兵在苏军的立体火力打击下,伤亡极其惨重,成建制地被消灭。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在钢铁洪流和绝对的火力优势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在这场战役中,臭名昭着的、从事细菌战研究的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731部队”,也偷偷摸摸地参与了进来,进行了他们第一次(也可能是少数几次)大规模的“实战应用”!据一些战后解密的资料和历史学家的研究,731部队的成员,曾在哈拉哈河战役期间,向上游水源中投放霍乱、伤寒、痢疾等致命病菌,或者通过飞机播撒带有病菌的跳蚤等媒介,企图通过这种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来削弱苏蒙联军的战斗力,挽回地面战场的颓势。这种丧心病狂、毫无人性的战争罪行,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苏军提前获取情报,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或者病菌投放的时机和效果不佳等),并没有在当时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反而日军自己为保守秘密,对自己士兵没有任何告知导致其1300多人感染细菌而死亡,真是“吃鸡不成蚀把米”。
诺门罕战役,最终以日军的惨败而彻底告终。据估计,日军的伤亡人数高达五万多人(其中阵亡和失踪近两万人),精锐的第23师团几乎被打残,大量的武器装备被摧毁或缴获。而苏军的伤亡虽然也不小(约两三万人),但在战略上却取得了决定性的完胜。
这场发生在亚洲腹地不毛之地的激战,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它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彻底打醒了日本陆军内部那些鼓吹“北进”苏联的狂热分子。他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红军远非他们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真要跟苏联全面开战,日本恐怕占不到任何便宜,甚至可能把自己给彻底搭进去。从此以后,“北进论”在日本军部内部彻底失势。
它使得日本军部内部,“南下派”的势力迅速抬头,并最终压倒了“北进派”。既然北边这条路布满了荆棘和陷阱,走不通了,那就只能掉过头来,把目光投向南边那些看似“软弱可欺”的欧美殖民地了。
它也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苏德战争的进程。因为日本在诺门罕被打怕了,所以当1941年6月德国“闪电”入侵苏联、希特勒一再催促日本从远东出兵夹击苏联的时候,日本军部始终犹豫不决,顾虑重重,最终没有下定决心出兵。这使得斯大林能够在莫斯科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放心地从远东军区抽调了数十万精锐的西伯利亚师增援莫斯科,这些生力军的到来,对扭转莫斯科战局、并最终粉碎德军的攻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朱可夫在诺门罕的胜利,不仅保卫了蒙古,也间接地为保卫莫斯科立下了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