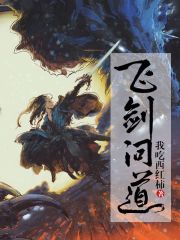拾光小说汇 > 二战那些事儿 > 第97章 十字军的试炼(第3页)
第97章 十字军的试炼(第3页)
这场被称为“托特”(德语“亡灵星期日”之意,因为战斗发生在11月23日,恰逢德国的亡灵纪念日附近,也有说法是指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让英军士兵感觉像是提前过了亡灵节)的遭遇战(广义上也属于“十字军行动”的一部分),再次展现了隆美尔在战场上那种化腐朽为神奇、以弱胜强的指挥艺术和“沙漠之狐”的狡猾本色。英国人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不成蚀把米,刚解围的图卜鲁格,还没捂热乎呢,又差点让人给端了老巢。
战线僵持,理想受挫
隆美尔的这次“回马枪”,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十字军行动”的整体走向,但也确实给奥金莱克和英国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官们,泼了一盆透心凉的冷水,让他们意识到,要想彻底打败隆美尔这个比猴还精的对手,绝非易事,光靠坦克多、飞机多是不够的,还得脑子转得比他快才行。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双方在昔兰尼加的沙漠中,展开了一场场激烈而又混乱的拉锯战。奥金莱克虽然也曾几次试图组织兵力,继续向西推进,希望能彻底击溃或包围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英军方面,虽然在兵力和装备上仍然占据优势,但他们也面临着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
补给线越拉越长,后勤压力山大:从埃及边境到昔兰尼加腹地,几百公里的沙漠运输线,对英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油料、弹药、粮食、饮用水……样样都缺。前线的坦克兵们,有时候渴得只能舔散热器里的冷却水,那滋味,估计比喝洗脚水还难受。
坦克损耗巨大,战斗力下降:在之前激烈的坦克战和德军88炮的“亲切问候”下,英军的坦克损失也相当惨重,很多坦克部队的战斗力已经大打折扣,不少坦克都是“带伤上阵”,跑着跑着就自己趴窝了。
情报误判频出,难以捉摸“狐狸”的踪迹:隆美尔的指挥风格,向来是不按常理出牌,充满了欺骗性和突然性,像个狡猾的赌场老千。英军的情报部门,虽然也能通过破译德军密码(比如那个着名的“恩尼格玛”)等手段获取一些情报,但往往难以准确判断隆美尔的真实意图和下一步的行动,导致在战场上经常陷入被动,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指挥分歧,协同不畅:英军高层(奥金莱克与前线的集团军、军级指挥官之间)在具体的战术运用和作战目标上,也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指挥,经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白白错失战机。
在这种情况下,奥金莱克最终还是放弃了继续向西穷追猛打的念头,命令第八集团军主力,在昔兰尼加的加查拉一线(位于图卜鲁格以西),构筑新的防线,暂时转入防御,进行休整和补充。他可能觉得,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先把到嘴的图卜鲁格给消化了再说。而隆美尔呢,也趁着这个机会,将他那支同样疲惫不堪、损失惨重的非洲军团,有序地撤退到了加查拉防线以西的艾格代比亚、阿盖拉等地,舔舐伤口,重整旗鼓,心里琢磨着:“英国佬,你们等着,等老子缓过这口气,下次非得把你们打回开罗去喝下午茶不可!”
“十字军行动”从1941年11月18日开始,到1942年1月初基本结束,持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这场战役,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试炼”,也是一场充满了遗憾和教训的“期末考试”。
英军方面,虽然成功地解围了图卜鲁格,将战线向西推进了数百公里,从战术层面上看,算是一次“胜利”。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人员和装备损失(据估计,英联邦军队伤亡约1万8千人,损失坦克数百辆),更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能够抓住机会,彻底消灭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主力。这使得隆美尔能够在短时间内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为后来英军在1942年春夏之交的加查拉战役和图卜鲁格再次陷落的惨败,埋下了伏笔。可以说,这是一次“战术上打赢了图卜鲁格,战略上却未能赢下昔兰尼加”的“未竟的反攻”,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德意联军方面,损失也同样巨大。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和意大利的几个军,在英军的猛烈攻势下,人员伤亡惨重,坦克、大炮等技术装备也损失殆尽。隆美尔被迫放弃了整个昔兰尼加东部地区,退回到了利比亚的西部。但他最宝贵的装甲主力,总算是保存了下来,为他日后的东山再起,留下了火种。他就像一头受了伤的饿狼,暂时躲进了洞穴,但那双在黑暗中闪着绿光的眼睛,却依然死死地盯着远方的猎物。
对于伦敦的英国民众来说,图卜鲁格的成功解围,无疑是一个值得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在经历了之前一系列的失败之后,这场胜利像一缕阳光,暂时驱散了笼罩在帝国上空的阴霾。报纸上又开始吹嘘“沙漠之鼠”的英勇善战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但对于丘吉尔和英军高层来说,他们心里却清楚得很,隆美尔这头“沙漠之狐”的威胁,远未解除,这根扎在帝国肋骨上的刺,依旧让他们寝食难安。奥金莱克虽然打赢了这一仗,但其指挥风格和作战效率,似乎也并没有完全达到丘吉尔的期望。丘吉尔对奥金莱克的信任,也开始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动摇,他开始在私下里,重新考虑中东战区的指挥架构问题,琢磨着是不是该换个更“给力”的将军来收拾隆美尔这个烂摊子。
据说,就在“十字军行动”的战报和总结陆续送到伦敦之后,丘吉尔在一次与军事幕僚的非正式谈话中,偶然提到了一个当时还在英国本土担任南方司令部司令、名气并不算特别响亮的陆军中将的名字。他似乎对这位将军在训练部队和强调纪律方面的严格作风,以及其在战术思想上的某些独到见解,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关注和兴趣。这个名字,就是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当然,在1941年底1942年初,蒙哥马利还远未成为那个后来在阿拉曼力挽狂澜、与隆美尔并称“沙漠双雄”的传奇人物。他的名字,只是在丘吉尔的脑海中,像一颗尚未发芽的种子,悄然地浮现了一下,等待着未来某个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
北非的沙漠,在经历了“十字军行动”的短暂喧嚣之后,又暂时恢复了它那特有的、充满了风沙和死寂的平静。隆美尔像一头撤入暗影中的沙漠狼,在黎明前蛰伏着,等待着下一次出击的机会,他相信,那句“命运的舞台”的台词,还没到谢幕的时候。而奥金莱克和他领导下的英国第八集团军,虽然暂时赢得了喘息之机,但他们能否继续守住这片在血与火中夺回的土地?能否彻底根除“沙漠之狐”的威胁?答案,即将在1942年春天揭晓。那将是一个充满了变数和风暴的春天,也将是一场更加残酷、也更具决定性意义的较量。谁能掌控沙漠之局的“十字路口”?命运的轮盘,又将转向何方?
喜欢二战那些事儿请大家收藏:()二战那些事儿